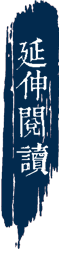一
《周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記》〈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大道不器」。皆以「道」、「器」對稱。
二
孔子曰:「君子⋯就有道而正焉」(〈學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衛靈公〉);有子亦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而〉)。可見孔子認為:君子用心所在,始終是原則性、目的性的「道」之本身,而非技術性、手段性的「器」所能換得的衣食、貧富等物質利益。
三
是以君子與人共事,必先確定彼此志同道合,否則「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堅持「與人為善」(不助人為惡)、「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見〈顏淵〉);即使出仕,也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絕不甘為御用工具,此所以君子亦必難進而易退(《禮記》〈表記〉、〈儒行〉)。因此,所謂「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必自居道體,絕不淪為器用;始終堅持自身道德的主體性,不容他人器使(被他人當作工具、從上或從眾作惡)。可見「君子不器」的真義,就是「君子不容器使」。
四
君子不容器使,甚至不容君上、父母將自己當工具。因此,君子事君上、事父母,必「敬」而非「順」。就事君上而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學而〉);子謂子產:「其事上也敬」(〈公冶長〉);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就事父母而言,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兩章皆見〈為政〉)在孔子看來,君子固應以「敬」事君上、父母,但是「順」並非美德。今人常講「孝順」父母,其實原始儒家只講「孝敬」父母。先秦典籍中,「孝順」一詞僅見於《國語》〈楚語上〉記楚大夫申叔時論教育太子之道,其中言及「孝順以納之」。但清趙翼《陔餘叢考》指出:「《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按:左丘明)特簡料而存之,非手撰也。」因此《國語》所載未必盡合儒家思想,此處之「孝順」便是一例。
五
孟子明言:「以順為正者,妾婦妾婦,泛指侍候人之「小人」。1 之道也」(〈滕文公下〉),就是從反面指出:罔顧是非的「順」順,順從、順服2 根本不是美德,絕非堅持「不器」的君子之道。君子不「以順為正」,當然既不媚上,也不媚俗。
就「不媚上」而言,孔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諫諍章〉)孟子更進一步推演此義:「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所以,當國君倒行逆施,真君子為了弔民伐罪,義無反顧,絕不顧惜被愚夫愚婦指責為「弒君」,而必奮起誅此「一夫」。
至於「不媚俗」,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孔、孟之言,皆鏗鏘有力,遠非今日馬英九、朱立倫這種「以順為正」之輩所能體解。馬、朱一味媚俗,不論是非,竟以不合「主流民意」為理由逼退洪秀柱,只能證明中國國民黨內已容不下真正的君子。
六
對於「君子不器」,傳統的解釋可以朱熹為代表。朱注此章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但即使「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通才),也還是一「器」(工具),只是「多用途」而已。如此將「不器」解為「不是尋常之器」,究屬牽強。朱注是秦以後的見解,應非孔子原意。在春秋時期,封建猶存,列國並立,「楚才晉用」是常有之事,良臣尚可擇主而事(孔子周遊列國,就是在找尋明主),君臣關係因此是相對的、可變的、有條件的,所以君子可以堅持「以道事君」而不被器使。這是「君子不器」的社會結構背景。到了秦統一天下,廢封建立郡縣,確立專制皇權,臣民不但不能擇君而事,也難以拒為君用,於是秦以後的儒家很難再堅持「以道事君」,「不器」就只好被解釋成「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這麼一來,「君子」說到底還是個「器」,只不過他是個「多用途的器」,可以使皇帝用得比較稱心如意而已。但這樣解釋實在是小看了孔子,同時也不能貫通理解其思想。
七
與朱注相比,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他的《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一書中直接把「不器」解釋成「不是工具」,反而比較貼近孔子原意。韋伯認為:「『有教養的人』(君子)不是『工具』,也就是說,在適應現世的自我完善之中,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實現某種客觀目的的手段。」參見洪天富譯,《儒教與道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頁275。3 但是韋伯此處對孔子「君子不器」的解釋,未必是他對儒家經典全盤掌握後的理解,而可能是得自康德(Kant)倫理思想(按:即應當把「人之所以為人者」當作一目的來看待,決不可只當作工具來看待)的啟發。所以,韋伯對「不器」一詞的解釋雖然正確,但是對「君子不器」的含意則引伸過度。韋伯認為:「儒教倫理的這一核心原則(按:即「君子不器」),拒斥了行業的專門化、現代的專家官僚體制與專業的訓練,尤其是拒斥了為營利得而進行的經濟訓練。」這等於是判定儒家思想與現代高度分工的社會不能並存,而這並非孔子原意。
因為,孔子雖然強調「義利之辨」(〈里仁〉),但他並不認為專業化毫無價值。只不過因為孔子教學的目的是使他的學生成為好的政治領導者(治國者),因此最重要的事當然是先成為「不器」的君子,而不是接受韋伯所說的專業化的訓練。例如,〈子路〉篇云:「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又如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可見在孔子看來,「上」(政治領導者、治國者)之首務應是修養「禮」、「義」、「信」,以「正其身」,而不是去學習「稼」、「圃」。但是孔子並沒有說「稼」、「圃」就毫無價值,只不過那是另一個領域(不在孔子教學的範圍內)的知識或技能。所以,馬英九在競選總統期間下鄉「long stay」,去學種田(即「學稼」),卻坐視整個國家和憲法的正當性日益流失而無所作為,這才是不務正業,正是孔子「鳴鼓而攻之」的對象。
八
孟子曾藉著談論百工技藝而發揮「君子不器」之義。孟子這一段話也可以用來證明儒家並不是反對「專業化」,只是反對「只講求專業,不講求是非」(自甘為「器」,不問目的)。《孟子》〈公孫丑上〉有云:「矢人矢人,做弓矢的工匠。4 豈不仁於函人函人,做甲冑的工匠。5 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巫,醫。6 匠匠,做棺木的木匠。7 亦然(醫師希望人活,棺木工匠希望人死)。故術不可不慎也(百工技藝如矢人、函人、巫醫、木匠,是以技術為他人服務,如果毫不考慮服務對象是君子還是小人、購買其服務或產品是要去做好事還是壞事,則很容易就會助紂為虐,成為壞人的共犯。因此,以百工技藝牟生者不可不慎於考量自己服務的對象和因自己的服務所造成的作用)。孔子曰:『里仁為美(學仁重於學技藝,故應近仁者而居,以求得其身教);擇不處仁(選擇住處時不選擇與仁者比鄰而居),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天爵,來自上天的尊嚴、尊貴地位。8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仁道至大至尊,無與倫比)而不仁(放著最高明、無可匹敵的「仁」而不學;「擇不處仁」,不向仁者學習),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就沒有是非對錯之心,於是就無所不可為,而可役於人或受人利用,甘為「器」用),人役(役於人者,即孔子所謂「器」)也。人役而恥為役,由由,即「猶」9 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一般做弓矢的人只為牟利,不論好人壞人來訂做弓矢,為了賺錢,一概服務,毫不考慮別人訂購弓矢的目的是做好事還是壞事,這就是「役於人」。做弓矢的人若恥於被人役使,就不能「不問是非,只問銀子」的盲目服務於人,而必須開始學習判斷是非對錯、選擇服務對象,這就是學習仁道)。如恥之,莫如為仁(如恥於為「器」,恥於「役於人」,那最好不過學習仁道)。仁者如射(「仁」是天爵,人世間的勝敗得失不足以左右仁者的尊貴,故仁者射箭目的在考驗自己,而非勝過別人):射者正己(比喻內修仁道)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第14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義也)」
九
在「器」與「不器」的問題上,最能見到中國和日本在根本價值理念上的差異。中國原始儒家標準下的典範人格(普遍當作被學習對象的人格)是「君子」,而君子講究「不器」,所以極力發揮「目的理性」,遇事先捫心自問,分清是非,絕不讓自己淪為工具。而日本一方面以「神道教」將「萬世一系」的天皇視為「現人神」(以人的形式活著的神),作為全民族信仰、獻身的對象;另一方面高倡「武士道」,講究對君上絕對效忠。實際上這就是「神化」天皇(即大和民族及大日本帝國的代表)、「器化」自己。於是,日本所推崇的的典範人格就是為了對天皇效忠而能將自己「徹底工具化」的「武士」。這種人不問目的正當與否,只要自己能發揮「功能」就好。日本軍國主義就是利用「神道教」加「武士道」,使全日本(連同其殖民地琉球、臺灣和朝鮮)徹底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
因此,同樣講「獻身」(devotion),中國的君子「獻身」於內心領悟的仁道(良心、良知),可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但對君上父兄卻可抗命不從;日本則倡導「獻身」於天皇(或長官、上司),所以能把自己徹底「器化」(工具化),不問是非而絕對服從,甚至泯滅人性、集體作惡。於是,中國的君子首重「目的理性」,其次才是「工具理性」,凡事要先問個是非對錯;但日本人則「工具理性」極其發達、「目的理性」極度萎縮,只要是「工作」、「任務」所需,日本人能做到正常人類所做不到的堅忍(對己)與殘忍(對人)。日本人可以不問國家走向、上級命令是否合理正當,而以盲目服從、徹底「器化」為榮。在戰時日本軍部要求官兵屠殺平民、參加神風隊自殺殉國;二戰後日本政府要求部分日本女性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阿吉是被幕府官員強迫與戀人分手,並獻給美國總領事的藝伎)那樣,為國家的利益獻出自己的身體和尊嚴,當妓女供美國占領軍泄欲取樂,這都是把人作為完全的「工具」看待。
日本既然能把本國人完全「器化」,當然也可以對別國人徹底「器使」,因此侵略、奴役、殖民、屠殺其他民族,甚至如「七三一細菌部隊」那樣把其他民族的人拿來做醫學活體實驗,或逼使大批其他民族的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對日本人來講都沒什麼不對,不覺得需要為其惡行道歉,甚至繼續把戰犯(個個都是「器化自己」的典範人物)供在靖國神社當烈士祭拜。就此而論,日本是個只講效率、不問是非的民族,因此,也是個沒有道德感(或「良心」)的民族(當然有道德感的例外是存在的,如家永三郎)。中華民族崇尚道德、敬重聖賢,大和民族則崇拜權力、美化(甚至神化)欲望。相對於中華民族講究「慎獨」的「罪感」文化,不講道德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可說是徹頭徹尾的「恥感」文化:做壞事只要不被發現就泰然自若,一旦被發現卻可為此切腹自殺。他們更喜歡集體作惡(奸淫擄掠、殺俘屠城),只要不為外人所知,就彼此互相遮掩,大家「心安理得」。如以「不器」做為「君子」的條件,則日本正是《鏡花緣》裡的「小人國」;如果把「道德感」做為「人類」的條件,則按照孟子所說的「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大和民族就是異於人類的禽獸(面對弱者時)、畜牲(面對強者時),是個只有「獸性」的民族。他們像一群螞蟻,每隻螞蟻都只追求自己這個族群整體的生存與擴張,並表現在對蟻后的絕對效忠與服從。
從「器化」角度,我們可以理解日本最駭人聽聞的特殊民族性:他們何以如此不尊重生命──不論是人類的生命還是鯨豚類的生命(後者見201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血色海灣》)。由於「工具」是「expendable」(可被消耗的)的,因此為達目的(不管這個目的是否正當)而犧牲、毀掉「工具」,正是「工具」發揮其最高價值的時刻。因此,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崇拜「死亡」、進而把「死亡」高度美化、藝術化來歌頌(如「櫻花飄落」)的病態民族。所以,殺人(如南京大屠殺殺掉三十萬中國人)與自殺(如二戰末期日本政府標榜的「一億總玉碎」),對日本人來講都不過是家常便飯。他們甚至可結合「殺人」與「自殺」,在二戰末期的冲繩戰役中逼迫琉球人「集體自殺」!他們殺人不眨眼,自殺也不眨眼──只要有助於日本這個螞蟻族群的壯大,任何人命都賤如螻蟻。從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歷史來看,日本這個民族的存在,是其周邊所有民族的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