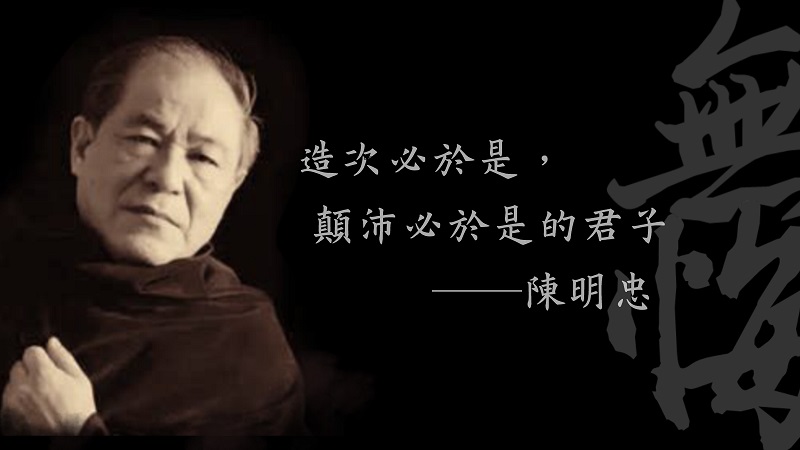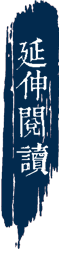一
「君子」、「小人」之分,是儒家對人所做的最根本分類,而「義利之辨」就是分類標準。「義」是道德,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擴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合理關係」,故《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五種人際關係為「五達道」(參見《論語》〈子罕篇.三達德〉);「利」是私利,關注的是「自己」。儒家先選擇要作個君子,決定從義而不從利,然後透過內省,在每一具體的人際情境中,依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君子愛人以德」來判斷何為義所當為。如果義、利發生衝突,君子必選擇從義。反之,不去辨別義、利,或從利不從義者,就是小人。此一「義利之辨」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最根本的差異所在。
二
西方人認為「道德」的性質不外以下二者(或者二者間不同比例的混合):
(一)道德是一種外在的客觀知識。
這種主張始於柏拉圖,認為「道德」(「善」)是外在的客觀存在。這類理論發展為各種哲學體系,由於所論被認為是「客觀」的知識,所以在理論上其目標是「普世」的(尤其是認為道德就是「神的命令」的各種神學),但弊病則是易流於專斷,成為部分人壓迫其他人的理論工具。換言之,這種道德實際上往往仍是部分人用來界定、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
此外,這種主張難以解決「知」與「行」的差距問題,無法回答:為何知道「道德」(或「善」)就能導致實踐它的動機?因為如果道德只是外在客觀的知識,完全有可能出現一位為了滿足其好奇心而研究「道德」的學者,對「道德」所知極多但人品極壞。事實上,我們可以討論「道德」,並獲得關於「道德」的某些知識(如我們現在在此所做的),但是道德在定義上(by definition)就與人的起心動念相關,因此不可能是外在於人的客觀知識。
(二)道德是發自內在的心理需求。
這類道德理論又分兩類,其一認為道德是基於人對他人的感情(同情或愛);其二認為道德是基於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動機。美國獨立宣言就乾脆將「追求幸福(happiness)」視為天賦人權之一。
但不論是基於感情或自利,這二者仍是出自一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其目標很難是普世性的,在實踐上充其量也只是屬於某一「我群」(we-group)的道德,對「非我族類」仍是不適用的。這在西方的民族主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以致於西方的民族國家通常「國強必霸」,一有機會就會發展成帝國主義。
西方哲學家中最接近儒家的是康德。他不但不把「道德」視為外在的知識,同時也不把幸福當作應當追求的道德目標。他認為一個有德之人會因其「道德的自我意識」(moral self-consciousness)而不得不(compelled)盡到自己的道德義務。但是他似乎把這種與幸福無必然關係的道德的「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視為另一種因內省(包括邏輯思辯)而得到的「知識」。於是又把「道德」外在化了。
把道德視為外在的「知識」,是邏輯上自相矛盾之事,在此不再討論。把道德視為心理需求,則是將道德視為某種「利」,以為道德可用「利益」來界定。
三
中國的君子知道「道德」(義)與「私利」(利)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判斷基礎,不能互相轉換,我們只能從「義」中反思出道德;西方人則始終誤以為可從「利」中提煉出道德。
西方人基於自身群體生活經驗,瞭解「一群完全自私的人不能群居共處」,「社會」的存在必須以克制私心的「道德」為前提。但是,他們不知「道德」與「私利」性質互斥,於是不做根本性的義利之辨,總是試圖在「私利」之上建立「道德」。結果,他們犯了兩類錯誤:
(一)以為「愛」可做道德的基礎:
西方人特別推崇人類天性中的「愛」(尤其是男女間的「愛情」、親子間的「母愛」),以為這就是「無私」,就可作為「道德」的基礎。其實,「愛情」或「母愛」不過是「放大了的我」或「放大了的『一己之私』」,愛的對象還是「我的情人」或「我的子嗣」,不是真正的「別人」。
西方人不知真正的「道德」必須從出發點便放下「一己之私」,因此惑於「為『愛』而犧牲」的行為,以為這種足以使人犧牲自己的「私愛」(愛情、母愛)就很偉大,堪為發展「道德」的出發點,於是西方人便致力於擴大(即前述「提煉」,或稱「昇華」)「私愛」,進而去愛「我的家族」、「我的鄉里」、「我的民族」、「我的國家」;如果附加上某些條件(例如:信「我的上帝」、順服「我的國家」),他們還自以為能夠做到「愛全人類」。
他們以為:某人「愛」的對象範圍越大,道德性就越高。事實上,由於其「所愛」的範圍(圓周)再大也還是以「我」為圓心,所以仍然是「私愛」(愛一己之私),因此,他們不可能真正愛「別人/異教徒/異族/異文化」。
例如,他們會說「在(我所信仰的)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但不信上帝者(或信其他品牌的上帝者)即無資格享受這種平等,於是也就得不到信上帝者的「愛」;他們還將自己的價值觀(包括宗教信仰)視做普世價值,把非西方民族視為「白種人的負擔」,扮演「十字軍」,用船堅砲利強迫其他民族「認識真理」、「信仰唯一的真神」,使許多非西方民族、非西方文化若不被其奴化或同化,即亡國滅種。
說到底,作為西方文化中「道德」之基礎的「愛」不論對象範圍多大,始終是「私愛」,是以「利」或「一己之私」為核心、出發點,因此只是「放大了的自私自利」,不是真正的道德。西方之所以有這個倫理學上的盲點,就是源自於他們不知義利之辨。
(二)以為各個人的「快樂/幸福」相加,就是「善」:
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放棄了傳統西方倫理學的道德觀,直接把個人的「快樂/幸福」之感覺視為「善」,並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視為最高的善,據此提出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這是西方人不知「義利之辨」而在哲學上最赤裸裸的產物。
然而,由於每個人的「快樂/幸福」感千差萬別,難以加總,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相互衝突,因此「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流於空話一句,最終導致功效主義的沒落。功效主義者試圖加總各個人的快樂感而從「私利」推導出「道德」,最後仍然失敗。
四
反之,整個中國儒家「道德」的基礎則是「義利之辨」。儒家先有意識地否定「『私利』可經過擴大、提煉、昇華、發展成為『道德』」,不認為「『利』可通於『義』」,於是便把「喻於義」和「喻於利」視作兩種迥然相異的價值思考方向,先把「別人」看做與「自己」在道德價值上平等(但未必在社會地位上平等);不從自己,而是從「平等的人」的人際關係裡反思倫理道德。換言之,西方人是在源自一己之私的「愛」(或是各個人一己快樂之總和)裡尋找道德,中國人則直接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裡反思道德。
因此,孔子雖然也講「愛人」,但這是「汎愛眾」(不是「愛自己的某某」)之「愛」,是直接把別人當做「與自己平等的人」來對待,是「『人』愛『人』」、「『人人』愛『人人』」,而不是西方人那樣「『我』愛『我的某某』」。所以,中國道德的核心價值觀念「仁」字從「二」從「人」,就是直指人與人(二人)間的關係(精確言之,是君子與君子之間的關係);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成了中國道德的金科玉律。
五
中國人思考道德問題既然不是從「我」出發,而是從「人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因此必然主張人人平等,不卑不亢。只是在實踐上,由於人對他人的理解力(同理心)、感受力(同情心)有限,故遠近親疏之別在所難免。因為「遠近親疏」無所不在,故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也無所不在,但是最終道德目標永遠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孟子一言以蔽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從「老吾老」、「幼吾幼」的差序格局出發,走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此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或張載所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
故中國人講的道德專注於「人人」(「仁」之本義),是真正「把人人都當人」的道德,緊扣住人與人間的「關係」;但西方人講的道德觀念則始終以「我」為核心,只是講求「如何把『一己之私』擴大」,甚至併吞其他人的「一己之私」。所以,西方人的道德基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始於個人的權利(rights);中國人的道德基於人人主義,始於每個君子對「人人」的責任(「以天下為己任」)。
所以,西方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我群」意識的民族主義(包括征服全世界的「使命感」),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人人主義的天下主義(天下一家,協和萬邦)。其結果,中國(包括國家與個人)再強大,也不會認為強凌弱、眾暴寡是應該的;而西方國家一旦強大,就會以對外擴張作為其「道德使命」。
六
在社會內部,西方人以為人人尊重別人的權利就是道德,但中國人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是道德。所以法國巴黎《查理週刊》以漫畫諷刺伊斯蘭教,自認為是其言論自由,但是卻違反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結果遭到恐怖攻擊報復,導致十二人死亡,十一人受傷。如果一個社會的秩序奠基於「權利」,除非維持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否則這種群際衝突勢必發生。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秩序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礎,就可以既開放而又和諧。
七
儒家知道「義」、「利」之不同,決定對其加以辨別,然後選擇「義」。他們自然會看到某些人(可能是大多數人)或者不知「義」、「利」有別,或者知道卻決定不加辨別,於是儒家提出「君子」、「小人」之分。這是儒家對人性最深刻、偉大的洞見之一:君子懂得「義」,於是只問是非;小人只懂「利」,因此只問得失。此與「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同義。
但一個人會成為君子還是小人,雖與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所受教育有關,說到底還是取決於個人內心道德性的選擇:若某人選擇認可「道德」的重要(也就是做出義利之辨),他就已決定要做個君子,然後他才會懂得道德與是非;若某人選擇不認可「道德」的重要(不做義利之辨),那他就始終是小人,人品不具道德性,只懂得利害得失。換言之,一個人先決定作君子(即決定分辨義利),然後才會聽懂「義」(「喻於義」);反之,一個人先決定作小人(即決定不分辨義利),那就無法聽懂「義」,只會逐「利」(「喻於利」)。
八
「道德」必基於自由意志,只能由個人內心自做選擇,無法由外在施壓、迫使他人產生道德心。盧梭認為強制人民服從「公通意志」(general will)是「強迫使其自由」(forced to be free),而黑格爾認為「絕對服從國家」才是「真自由」,二人都認為可經由強制而提高人民的道德性,都是完全曲解了「道德」的本質。因此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面對自甘為小人者,不論如何講解「道」、灌輸「道」,也改變不了他的格局,無法把他從小人變成君子(「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