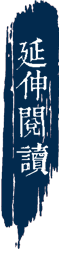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北京專條》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認為此一條約既承認了日本出兵臺灣的正當性,也斷送了琉球的主權。1他們得出此一結論的原因,通常在於把琉球漂民遇害作為日本出兵的唯一原因,從而對《北京專條》的解讀便因此扭曲。但是香港學者梁伯華及大陸學者陳在正則以史料駁斥了這種錯誤認知。以下,我們以這兩位學者的論證為基礎,還原歷史真相。
在解讀條約文本前,我們要注意兩件事。首先,此一條約只有中文本,顯示中方是主要的起草者,因此其文本解釋當然必須合乎中文語意,別無他解。而在當時談判中,中方已經對日本人的狡詐提高警覺,所以即使實質上委曲求全,但在條約用字上則字斟句酌,步步設防。因此,我們不僅要注意條約中寫了什麼、如何寫,更重要的是條約沒有寫什麼、為何不寫。
其次,如前所述,日本在1874年2月的《臺灣蕃地征伐要略》中確實寫著:「報復殺害我藩屬琉球人民之罪,為日本帝國政府之義務。」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僅以琉球國漂民遇難作出兵藉口實過於薄弱(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琉球不但向中國致謝,還向日本抗議其出兵犯臺),於是在同年4月5日給西鄉從道的詔諭中便將出兵藉口改為兩項:1871年「我琉球人民漂流至臺灣番地,為當地土人所劫殺者達五十四人」,及1873年「我小田縣下備中州淺口郡居民佐藤利八等四名漂流其地,衣類器財亦被掠奪」;4月10日日本外務卿給英國駐日公使覆函,亦解釋出兵理由是琉球與小田縣兩起漂民「或被劫殺,或則衣服、器材被掠奪」;福島九成於5月4日在廈門遞交西鄉從道致閩浙總督李鶴年的照會亦是兩案並提;以後所有給中國的照會、函件以及日軍在臺灣登陸後的安民布告也一直是兩案並提。反之,中方給日方的歷次照會及在談判桌上的辯論,也都兩案並駁,始終主張:一、琉球是中國屬國,其漂民遇難與日本無關;二、日本小田縣民無一被殺,且已被妥善送還;三、臺灣全島都是中國邦土,「生番」問題應「由中國自辦,無庸貴國代謀」。在與琉球有關的問題上,中方始終把琉球國民與日本國民嚴格區分。2
於是,我們可以正確解讀《北京專條》如下:
一、最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專條》從頭至尾一字不提「琉球」。這在日方如此重視藉「琉球漂民遇害」來彰顯琉球屬日的情況下,絕非無意之舉。實際上,這就是中國堅持此約不涉及琉球作為中國藩屬國地位的體現。因此,將此條約解釋為「承認琉球屬日」或「中國斷送了琉球主權」,完全違反史實與法理。大多數人是因後來日本在事實上併吞了琉球,才按照日方後來的刻意曲解來逆推解釋該條約。但是在1874年,日本的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在簽約後於自己12月15日的記載中還表示:《北京專條》的内容與日本對琉球主權拉不上法理關係。3由於「生病的強盜」急於脫困,梁伯華指出:「事實上,大久保利通在談判時一心一意想將臺灣危機立刻解決,他甚至千方百計避免將琉球問題扯入交涉之中,以免節外生枝。」4換言之,雖然「事件」(臺灣出兵)與琉球有關,但是「條約」與琉球地位無關。
二、《北京專條》前言中寫道:「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爰定此「退兵並善後辦法」。其中「日本國屬民等」一語,特別加了「等」字,表示除了「日本國屬民」(日本小田縣藤利八等四人)外,還包括「非日本國屬民」的琉球漂民。因此,此段文字只能解釋為遭難者「不只日本國屬民」,而不能解釋為中國承認琉球人也是「日本國屬民」,否則這裡的「等」字就沒有意義了。並且,「退兵」與「善後」並提,中方顯然是以日本退兵為相對條件而答應善後條款(即對日本受難者的「撫恤銀兩」及對日本軍費的「籌補銀兩」共五十萬兩,對琉球人的撫恤則將由中琉另議),並且在會議憑單中明文規定:到12月20日,「日本國全行退兵,中國全數付給。均不得愆期。」在此可以見到日方《臺灣蕃地征伐要略》第六條(邊談邊打原則)帶給中方的陰影與戒心。
三、條約第一條為:「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此處的「民」,等同於前言中的「日本國屬民等」及第二條的「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但是超過會議憑單中的「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因為還包括了「非日本國屬民」的琉球漂民在內。並且,「中國不指以為不是」隱含的前提是:本來日本此舉(違反《修好條規》,侵犯中國邦土、干預中國內政)並無正當性,因此「中國有權指其為不是」。而中方為何肯「不指以為不是」?因為承認日本犯臺的「動機」「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並且姑念日本原先不知道「生番」地區也屬於中國,於是(在日方守約退兵的前提下)中方暫不計較日方侵犯中國邦土。那麼,為什麼「臺灣出兵」可稱「義舉」?陳在正指出:「所謂『義舉』,指『復仇仗義』,可以包括為友好鄰國(按:指琉球國)打抱不平。」中方在10月20日與大久保第六次談判中,提出《節略共五條》,其中指出:「貴國先不知番土係中國地方,故為復仇仗義而來。今日既知係中國地方,中國又允為自辦,又為修好仗義而去。」於是,中國費盡心思,以「不知者不罪」為由幫日本找了個「義舉」下台階,但是終究沒有承認「化外為無主地,日本有權侵占」,更沒有承認琉球人也是「日本國屬民」。5
四、條約第二條為:「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按:指條約附件「會議憑單」)。」注意這裡的用詞並非「賠償銀兩」,因為中方並未承認日本有權出兵犯臺,中日也未交戰所以沒有「戰敗國」,因此不論琉球漂民之死或日本用兵之費,中國皆無「賠償」義務,僅僅是為了買得強盜退兵,不得不對日「讓利」。換言之,這五十萬兩銀幾乎可視作贖回臺灣的贖金。只是,由於「臺灣出兵」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次對外侵略,雖然中方沒有答應日方提出的兩百萬兩銀,但這個經驗多少讓日本體會到「戰爭有利可圖」(只要強盜不生病)。下一回,在馬關議和時,日本就獅子大開口了。
五、中國在前言「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行查辦」的前提下,於第三條中承諾:「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兇害。」由此,臺灣的「生番」地區終究確定屬於中國主權範圍。遺憾的是,面對日本這樣的禽獸之國,中國當時已不夠強,不僅藩屬不保,連版圖也瀕危。最後琉球、臺灣、朝鮮皆相繼淪為日本殖民地。
六、在會議憑單中規定:「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中國先准給撫恤銀十萬兩。」由於中方嚴格區分琉球與日本,可知此處的「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並不包含琉球遇害漂民。但是後來,中方還未履行對琉球遇難漂民「定給撫恤銀兩」,日本就併吞了琉球。反之,日本為了表現「心中有琉球」,象徵性地以汽船、粟米等物折算給琉球,卻被琉球拒絕。6
以上就是基於史實與法理對《北京專條》的唯一正解;事實上,這也是當時日方代表大久保利通的理解。《北京專條》簽訂後,大久保於11月7日到滬向江海關領取撫恤銀十萬兩。11月24日,西鄉從道下令撤軍,12月2日日軍及後勤人員全部撤出臺灣。712月16日,清政府向日方付款四十萬兩。這一次,強盜沒有得逞。
但是,《北京專條》跟所有的條約、公報、協定一樣,可防君子但防不了小人。當大久保利通完成了簽約、拿錢的任務回到日本後,於1874年12月向日本政府上奏時還說:「今者中國承認我征蕃為義舉,並撫恤難民,雖似足以表明琉球屬於我國版圖之實跡,但兩國分界,仍未判然。」實際上這就是承認《北京專條》並非為解決琉球地位問題而訂。只是小人不會止步於條約之共識,大久保接著就建議:「可先召其(按:指琉球)重臣,諭以征蕃事由及出使中國始末,使令藩王宜自奮發,來朝覲謝恩。且斷絕其與中國之關係,在那霸設置鎮台分營,自刑法、教育以下以至凡百制度,逐漸改革,以舉其屬我版圖之實效。」8為了繼續製造琉球「屬日版圖之實效」以積非成是,1875年3月,大久保便採納日本的法籍法律顧問巴桑拿(Gustave E. F. Boissonade)的歪主意,開始扭曲詮釋《北京專條》,將「保民義舉」曲解成中國承認琉球屬日,以便作為日本併吞琉球的「法理根據」。9但是,談判紀錄史實俱在,這只是再度證明了沒有道德意識的日本人不可信賴。
當時的名人王韜寫了一篇〈琉球向歸日本辨〉,指出:日本「討罪臺灣,尤昧於理。其始託言劫掠小田縣民,繼乃及琉球漂民;我朝大度包容,勉徇英國公使之請而成和議。其所定條款兩端,未嘗一字及琉球;載在盟府,人所共見。乃遂欲以此指琉球為日本屬地,掩耳盜鈴!」10王韜這段話明確反映了當時中國人認知的事實:琉球為中國藩屬,《北京專條》與琉球地位無關。中國政府一直强調此點,即到了後來1880年1月13日當英國駐日大使巴夏禮晤日本外相寺島宗則時,還引述中國政府所强調的《北京專條》中的撫恤銀兩是對小田縣漂民而非琉球漂民,而這段記載出現在1879年日本因併吞琉球(「廢藩置縣」)時派遣宍戶璣赴華談判後所輯成的《宍戶璣關係文書》之内。事實上,《北京專條》若真是解决琉球問題的法理文件,日本根本不需要派宍戶璣與中國再談琉球問题。11
然而,「大信不約」只對君子之國的中國有效。對日本這種信奉弱肉強食的民族,白紙黑字的條約也形同廢紙。12如同美國以其片面規定的「規則」大於一切國際法,日本私下制定的《臺灣蕃地征伐要略》也高於公開簽訂的《北京專條》。該《要略》第三條規定:「阻止琉球遣使納貢之非禮,可列為征伐臺灣以後之任務。」於是,大久保內務卿一方面依據巴桑拿的意見虛構「中國承認琉球屬日」,另一方面召琉球三司官到東京。1875年3月底,琉球三司官到達東京,大久保告以將賜以汽船或粟米來「救恤難民」,並要琉球王來東京朝覲,遭琉官婉拒。5月9日,日本政府發出如下五條命令,立即實行,即:廢止對中國朝貢;撤銷福州琉球館;廢止琉球新王受中國冊封;令琉球王來朝覲;琉球與中國交涉概由日本外務省管轄。6月再派內務大丞松田道之到琉球傳達上述命令。據日方記載,9月間琉球三司官對大久保利通提出:「琉球藩久荷中國恩誼,今不能無故背棄。天朝(按:指日本)若與中國交涉,如得中國承認,則當奉命。」然而,大久保無法證明「中國承認琉球屬日」,便直接「不許」。迫於壓力,琉球王尚泰於是年11月派其弟尚弼至東京,上謝表,獻方物。13為防範琉球向中國求援,日本從1876年起更命令所有琉球人往中國者需先向日本申請「海外旅行券」(即護照)。而日本對琉球的管理亦由外務省轉到内務省,為吞併琉球鋪路。
琉球的最後希望就是向宗主國中國求援,以存國祚。因此,尚泰王密遣特使向德宏及林世功來華,於1877年4月12日抵福州。清廷接獲巡撫何璟及總督丁日昌奏報日本「阻貢」後,於6月24日詔令首位駐日公使何如璋到任後「相機妥籌辦理」。該年正逢日本薩摩之亂(1877年2月-10月),亂平後何如璋與參贊黃遵憲等始出發赴日。12月7日抵神戶停泊,夜間琉球國使臣來謁,痛哭求救,何如璋與黃遵憲頗受觸動。14待何、黃到任後,對日本永不滿足的擴張野心及其與日俱增的國力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更體會到日本染指琉球只是它對外擴張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朝鮮和臺灣,於是前後致書總署及李鴻章數十函,主張強硬對日,保住琉球。
何如璋在〈與總署總辦論球事書〉中首先指出日本的野心絕不會止於琉球:「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已滅,次及朝鮮。……況琉球迫近臺灣,若專為日屬,改郡縣、練民兵、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即為臺灣計,今日爭之,其患猶紆。今日棄之,其患更亟也。」因此,務必在琉球擋住日本的野心。何接著提出三策:「為今之計,一面辨論,一面遣兵舶,責問琉球,徵其貢使,陰示日本以必爭,則東人氣懾。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據理與爭,止之,不聽,約球人以必救,使抗東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師應之,內外夾攻,破日必矣。東人受創,和議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聽,時復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評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僥倖圖存,此下策也。坐視不救,聽日滅之。棄好崇仇,開門揖盜,是為無策。」15
然而當時中俄關係因伊犁問題愈趨惡化,在南方則與法國於越南問題上相持不下(後來導致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李鴻章等洋務派正幻想聯日抗俄,不願力保琉球,認為何所提上中兩策「小題大作,轉涉張皇」。16因此何如璋也唯有採用下策,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交涉琉球問題,但是日方根本不在意「理屈」。最後何在1878年10月7日向日本外務省遞交一份措詞強烈的抗議照會:「琉球國為中國洋面一小島,……貪之無可貪,併之無可併。……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臣服中國,封王進貢,列為藩屬。……咸豐年間,曾與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荷蘭國立約,約中皆用我年號曆朔文字,是琉球為服屬我朝之國,歐美各國無不知之。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竊念我兩國自立《修好條規》以來,倍敦和誼,條規中第一條即言『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互有侵越』,自應遵守不渝,此貴國之所知也。今若欺陵琉球,擅改舊章,將何以對我國?且何以對與琉球有約之國?……方今宇內交通,禮為先務。……務望貴國待琉球以禮,俾琉球國體政體一切率循舊章,並不准阻我貢事,庶足以全友誼,固鄰交,不致貽笑於萬國。」17
問題在於日本正是「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的專業戶。外務卿寺島宗則反而以這份照會「無禮」為藉口,要求何如璋書面道歉,否則停止商談,實際上是在觀察中方反應。但中方實無更有力的辦法,於是日本決定強制兼併琉球。1879年3月27日,日本琉球處分官松田道之在琉球首里王城對琉球王宣布廢琉球藩,4月4日明治政府正式宣布改琉球為沖繩縣。尚泰王被迫遷至東京,琉球遂正式亡國!18
此時,李鴻章得知甫卸任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將來華訪問,遂又動起「以夷制夷」的妄想,希望請打開日本國門的美國之卸任總統出面調解琉球問題。李在5月28日及6月12日兩晤格蘭特,格氏其實不瞭解琉球問題涉及的宗藩體制,輕率答應赴日斡旋。面對日方以西方國際法(包括曲解的《北京專條》)來反駁中國的宗藩體制,格氏只能致函中日雙方,呼籲重開談判。日本反正「靠實力說話」,答應派駐華公使宍戶璣與中國總署大臣談判。結果總署並未徵詢李鴻章,即於1880年10月與宍戶璣簽訂「分島改約」的草案,而其主要內容是將琉球群島最南端的宮古島和八重山群島割給中國,但是中國必須同意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前者因兩島小而貧瘠,無法達到中方「存琉祀」的目標,後者將助長日本侵華野心,遭到李鴻章等大臣極力反對。最後李鴻章於11月11日上奏:「琉球初廢之時,中國以體統攸關,不能不亟與理論;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為相宜。」19
琉球使臣林世功為了阻止清廷簽約承認琉球亡國,於1880年11月20日留下絕命詩二首後自殺殉國。日使宍戶璣則對清廷「延宕」手法極為不滿,在1881年初離華返日以示抗議,並謂今後日本再不會與中國商討琉球問题。
法理上,中國從未承認日本併吞琉球國,遂使「球案」成為懸案。但是事實上,清廷在何如璋抗議無效後採取的正是何所提三策之外最糟的「無策」,即「坐視不救,聽日滅之,棄好崇仇,開門揖盜」!當時何如璋還說:「琉球苟滅,後患滋深,是不爭所以萌邊患。」20結果一語成讖。十五年後,臺灣澎湖俱隨琉球之後淪於日手!然後中國人(包括李鴻章)才知道日本實為中國之大患,而琉球在地緣政治上實為中國臺灣之屏障,唇亡則齒寒!
柳暗花明的遺骨判決
琉球人和中國人一樣,都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曾經共同創造了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當時,琉球作為一個獨立王國,是天下秩序中的「守禮之邦」,也是東海上的「萬國津梁」。但是這個獨立的琉球國,在1609年被日本薩摩藩挾持,1872被迫成為日本的藩屬,1879年更被日本違反琉球人的意願而併吞為殖民地。其後歷經二戰末期的沖繩戰役、歷時27年的美國軍事占領及管治,1972年又被美國「返還」日本,繼續進行第二次殖民統治。換言之,琉球人作為一個民族,從1872年以來,就被剝奪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因此,所謂「琉球地位問題」的唯一合理解決方案,就是承認琉球人是琉球群島上的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使其有機會回歸其歷史上的原有地位,恢復為一個獨立國家。事實上,依照二戰期間的《開羅宣言》21、《波茨坦公告》22和1945年的《日本降伏文書》23,琉球本應在日本投降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後在適當時機行使自決權決定其地位。可是,美國為了其冷戰時期的軍事需求,在舊金山議和時與日本私相授受,由美方提出日本對琉球仍有「剩餘主權」之說,然後不經聯合國的託管程序,由日本單方面將琉球的管治權交付美國,後來再由美國將琉球群島分段「返還」日本,但仍保留大量的駐琉美軍基地及特權。
如今,牡丹社事件已過去了一百五十年,琉球人至今還在日本與美國的雙重殖民統治之下,臺海兩岸關係也繼續被美日干擾、離間。既然東亞秩序的崩解、制中「第一島鏈」初建始於日本藉犯臺以併琉,那麼重建東亞國際秩序當然也必須完成於臺灣回歸中國與琉球脫離美日。現在,中國的統一已經是進行式,那麼琉球的未來呢?
日本第一次對琉球進行殖民統治(1879-1945)時,京都帝國大學助教授金關丈夫以「體質人類學」研究之名,於1929年在琉球各地盜掘、收集琉球人先祖的遺骨,藉虛偽的「學術研究」為日本的殖民主義服務。這些琉球人遺骸,分存於金關服務過的臺北帝國大學及京都帝國大學。近年經過琉球族人的不斷努力,其中收藏於臺灣大學(原臺北帝國大學)的琉球人遺骸,終於在90年後的2019年回到了琉球,但卻是由日本主導的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負責接收及存放,並未歸葬原址。24京都大學(原京都帝國大學)則根本拒絕「琉球民族遺骨返還研究會」的代表松島泰勝教授檢視這些遺骸,當然更不願返還。
為使祖先遺骸得以重新安葬原鄉原址,松島教授及與遺骨相關的琉球人對京都大學和沖繩縣教育委員會提起訴訟,大阪高等法院及那霸地方法院分別於2023年9月22日及28日作出判決。那霸地院判決基本滿足了琉球人的訴求,但是大阪高院則以原告無法證明自己是遺骸合法所有人而判其敗訴。然而,在大阪高院的判決中,首度出現「沖繩地區原住民族琉球民族訴訟人們」,並且承認「昭和初期沖繩受到大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這是日本國家機關第一次在公文書上承認琉球民族是原住民族以及琉球曾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而且還承認原住民族的遺骨返還是一個全球性趨勢,遺骨應當回到其「故鄉」琉球。為使這段重要陳述得以定讞,原告決定放棄上訴,以使琉球人作為原住民族的地位取得日本國內法的依據。
與日本曲解版的《北京專條》剛好相反,大阪高院的判決明確無誤地承認了琉球人(異於日本人)的原住民族地位與被殖民處境。現在,關鍵就在中國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如何應對這個判決的法理意義了。如果妥善因應,這個判決可能成為推進解決琉球問題的里程碑。
首先,中國從未承認19世紀時日本併吞琉球,也未受邀參與戰後的舊金山議和,1951年8月15日中國外長周恩來還正式聲明:《舊金山對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25後來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中國仍然堅持此一立場。因此,中國當然可以聯合其他不承認《舊金山對日和約》的二戰時盟國,依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降伏文書》,主張琉球不屬於日本,並且幫助琉球民族改善其處境,直至自決復國。由於琉球本來就不應在日本主權範圍內,因此作此主張並不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之規定。
如今,大阪高院判決既已承認琉球民族的原住民族地位及日本對琉球進行殖民統治的事實,中國現在就可以開始在各種聯合國相關機構與會議上,聯合其他不承認《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戰時盟國,直接引用此一判決來聲討美國、日本聯手迫害琉球民族的作為。
首先,中國可要求日本依據此一判決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26,從立法及行政措施上確保琉球民族的各種應有權利,特別是按照該《宣言》第30條「不得在原住民族的土地或領土上進行軍事活動」(Military activities shall not take place in the lands or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之規定,要求遵循琉球民族的意願,撤除琉球群島上的所有軍事基地,以實現「原住民族土地和領土非軍事化」(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lands and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使琉球人永不再受戰爭威脅。其次,中國可再引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降伏文書》,主張琉球不應屬於日本主權範圍,並引用大阪高院判決,確認琉球仍為日本殖民地,然後向聯合國提出將琉球列為「非自治領土」,納入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監督。與此同時,中國應加強與琉球的文化和經濟交流,幫助琉球人恢復其固有文化,並改善其經濟處境,以此一方面加強琉球人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減低琉球對日本的經濟依賴。最終,當美國霸權在東亞消退,日本亦不再能在琉球為所欲為,中國即可協助琉球內部的復國運動人士向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提出公投自決要求,最終決定琉球復國,使整個東亞國際秩序回歸正軌。
如果東亞地區愛好和平的國家都能體會琉球復國運動對建立東亞和平秩序的重大意義,那麼2023年9月22日的判決將會是東亞歷史的轉捩點。
一百五十年前由牡丹社事件開啟的東亞動亂惡夢,或許已經出現了曙光。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回顧牡丹社事件以來的歷史,我們能學到什麼?
首先,明太祖是對的,何如璋是對的,聞一多也是對的——琉球重要!琉球很重要!!琉球真的很重要!!!
因為日本是東亞內部的禍源,並藉由侵占琉球破壞和平秩序,所以位居要衝的琉球必然是東亞和平的鎖鑰。明太祖主動招撫琉球,何如璋警告「琉球苟滅,後患滋深,是不爭所以萌邊患」,聞一多在《七子之歌》中寫下:「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眞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臺灣」,都是一個意思。
施琅在〈臺灣棄留疏〉中指出: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換言之,失去臺灣,中國東南沿海就難以發展;但是琉球若屬日,則「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骨牌效應,琉球茲事體大!日本占琉球,真正的目的就是取臺灣,所以臺灣若要長治久安,務必使美日退出琉球,琉球人心向我。
總之,只要日本的靖國神社還在,日本人自認「神國」可恣意肆虐的禽獸文化基因就隨時蠢蠢欲動,中國就絕對不能忽視琉球。
其次,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2024年2月17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中所言:「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27在這種「現代國際秩序」下,「以夷制夷」的必要前提是:自己夠強,不在「菜單」上。否則,中國地再大、物再博,也只是列強環伺下的一桌滿漢全席!此時幻想「以夷制夷」,只會引狼入室,徒讓諸「夷」分進合擊分食我國。看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瓜分豆剖的歷史,就知道這個道理。
因此,在牡丹社事件後,王韜在〈琉事不足辨〉中寫道:「西人之左袒日人,要非無故。我朝所有屬國凡五:越南也、暹邏也、緬甸也、高麗也、琉球也,皆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今自琉球、高麗(按:此二者俱為日本覬覦者)外,越南則據於法矣,暹邏、緬甸則據於英矣。蠶食鯨吞,方且日事侵削,安知其後不為琉球故轍乎?故以琉事折衷於西人,計之左也。」28事實上,在「臺灣出兵」後期,在臺日軍已左支右絀,幾乎全員病倒。29如果中國情報工作做得好,知己知彼,那麼大久保最後裝狠,中國大可不理,等著日軍自行撤退。結果英使威妥瑪出面,不但讓日本有了下台階(五十萬兩銀),還讓中國欠英國一個「人情」。並且,如同日本的法籍法律顧問巴桑拿為大久保出主意曲解《北京專條》作為吞琉「法理基礎」一樣,英國人也樂見日本併吞琉球,畢竟英國不只抓著暹邏、緬甸,連西藏都在它的「菜單」上。
更荒誕的是當日本正式併吞琉球後,李鴻章居然想找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斡旋。實際上,在牡丹社事件中,原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不但為日本提供地圖、國際法「法理」30,及他因「羅妹號」事件幾度來臺探查、交涉的經驗,當1873年副島種臣及柳原前光來華為翌年的臺灣出兵試探中方時,李仙得根本就是隨團顧問。31後來在「臺灣出兵」期間,因為李仙得高度涉入日方謀劃,違反了國際法戰時中立原則,被美國駐廈門領事逮捕,而美國國務院卻發公函下令釋放。以上這些事,都發生在格蘭特任內,他不可能不知情。並且,由於李仙得過於招搖,甚至陪同日本使節會見中方官員,中方亦知美國並不中立。1874年6月14日文煜、李鶴年及沈葆楨聯名上奏時就提到:日本「所以敢於鴟張者,則又窺中國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國暗中之資助。」32然而李鴻章竟然相信格蘭特會幫中國向日本爭琉球!
就此而論,新中國的抗美援朝及兩彈一星都是性命攸關的壯舉。如果沒有這種鬥志、這點底氣,中國連「被利用」的價值都沒有,只能像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一樣永遠當附庸,隨時可被拋棄。
於是,我們可總結出第三個教訓:「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
帝國主義就是強盜。面對強盜,講道理、國際法、聯合公報、條約都不能單獨生效,因為強盜的語言是「實力」。自身若實力不足,不要說濟弱扶傾,連自保都難。此時,講理絕對無效,國際法比不上「規則」,《八一七公報》後面躲著個「六項保證」,《中日修好條規》被利用為侵略的工具,《北京專條》則形同廢紙。33
李鴻章在前兩點上都犯了錯,但是他說對了一件事。就在初見格蘭特的十天前,李鴻章在1879年5月18日給丁日昌的信中講到一次與清帝的應答:「上詢:琉球事當若何?對:惜我無鐵甲船,但有二鐵甲,闖入琉球,倭必自退。上謂:外廷皆力言鐵甲不可購造,糜費無益。對:至此可知有益,但既無巨款,亦來不及也。」34區區「二鐵甲」,硬是讓一個幾千年的文明古國在一隻禽獸面前抬不起頭來!看來,李鴻章寄望於格蘭特也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
今天的中國,有了遼寧艦、山東艦、福建艦,這是三艘超級鐵甲,還有新型兩棲攻擊艦、第五代殲擊機……,這才是硬道理,是侵略者聽得懂的語言。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對侵略者終於不再「失語」!
當然,歷史的教訓也有另一面。我們與禽獸為鄰,目睹日本維新崛起、囂張狂妄、四面出擊、燒殺擄掠,直到毫不冤枉地挨兩顆原子彈,戰敗投降;然後,它藉助朝鮮戰爭及冷戰,又在美帝扶持下再成軍事強國,軍國主義原形再現,右翼再度得志猖狂,準備重蹈覆轍。
所以,中國必須「硬」的有道理、有道理的「硬」。否則,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那麼,既然硬道理也需要有道理,我們就必須把中國的道理講清楚。
1951年8月15日,周總理在〈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中說過:《和約》草案「保證美國政府……獲得對於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硫黃列島、西之島、沖之鳥島及南鳥島等的託管權力,實際上就是保持繼續占領這些島嶼的權力,而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的。」於是,某些美日代言人就喜歡抓住最後這句話,然後主張基於「禁反言」原則,中國不可主張琉球應脫離日本。但是,首先我們要注意周總理的用字是「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而非「未曾被規定應脫離日本」,更不是「曾被規定應屬於日本」。換言之,原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要使東亞秩序合理化,以確保和平,因此才規定「臺澎及東北應歸還中國」、「韓國應獨立」、「日本的領土應限於四大島」(故應不包含琉球),當然不能容許美國為著「美國第一」的自私考量,藉著一個不合法的「和會」把琉球拿來當軍事基地使用。因此,所謂「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意思是在1951年時,使其終局脫離日本的適當時機及合法程序尚未出現,但不代表中國反對琉球「應脫離日本」,更不代表中國支持琉球「應屬於日本」。
於是,周恩來講這句話的時空背景就值得注意。當時,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剛開始實施,基於該憲法第九條,日本原本應該永遠告別軍國主義,而且不應擁有軍隊、發起或參加任何戰爭。反之,在美國主導下出台的《舊金山和約》,將會確保美國能夠利用琉球作為前沿軍事基地,而長期威脅東亞和平。因此,周恩來對《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反對,是基於以下兩點原則:
一、在程序上,1942年1月1日的《聯合國家宣言》「規定不得單獨媾和,《波茨坦協定》規定『和約的準備工作』應由在敵國投降條款上簽字之會員國進行。35……但是,美國政府在長期地拒絕實施《波茨坦協定》原則以拖延對日和約的準備工作之後,竟由美國一國包辦了現在提出的這一對日和約草案的準備工作,而將大多數對日作戰國家尤其是中蘇主要對日作戰國家,排斥於和約的準備工作之外,並由美國一國強制召開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的和會,企圖簽訂對日的單獨和約。」換言之,這個「和會」在程序上是非法的。
二、在實質上,《和約》草案「在領土條款上是完全適合美國政府擴張占領和侵略的要求的」,「實際上這是一個準備新的戰爭的條約,並非真正的和平條約。」
可見周總理的真意,是反對琉球群島被美國當作軍事基地使用(而這種軍事占領的擴張行為,居然是由一個《和平條約》來保證);所謂「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的」,也是假設日本在「和平憲法」下將徹底非軍事化。在這兩個前提下,中國當然反對美國透過一個不合法的「和會」,從日本手中接管琉球。
總之,周總理這句話不表示中國承認琉球就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或應該永遠屬於日本——即使日本違反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還撕毀了《降伏文書》和它自己的「和平憲法」。中國在意的始終是東亞地區合理的和平秩序,反對「準備新的戰爭」的假《和約》(導致後來「冷戰」下的假「和平」,以及韓國、中國的長期分裂)。後來,日本在美國的卵翼下很快又現出原形,否定過去的戰爭罪責,公然祭拜戰犯、重新建軍,露出軍國主義的獠牙,導致許多的「應該」尚未成為事實,更多的「不應」卻已積非成是——琉球「返還」後美軍基地還在,「和平憲法」未改而日本已成軍事強國,日軍甚至已進駐琉球群島。既然中國反正從未承認過日本的「琉球處分」、舊金山會議及它通過的假《和約》,那麼,基於同樣促進和平的原則,中國現在反對美日繼續在琉球群島駐軍、支持琉球民族自決脫離日本,又有何不合理或前後不一?
1870年9月總理衙門曾以「大信不約」婉詞謝絕日本的訂約要求。但日本民族性中少了那點「幾希」,永遠不會懂這四個字。「大信不約」出自《禮記》〈學記〉,不是主張不需守信,而是強調必須反思「守信」與否的目的價值何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如果彼此與人為善、推己及人,自然就能和睦相處。這種情況下的「約」,才值得守;一旦情勢變化,守約反而造成不公正或不合理時,那麼也可改約或甚至違約。據《左傳》記載,西元前607年(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言行不像個國君),……宣子(趙盾)驟諫,(晉靈)公患之,使鉏麑賊(殺害)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刺客鉏麑受晉靈公之命而去暗殺趙盾,當他發現趙盾是晉國百姓的好領導後,面臨兩難困境:他若不執行君命而放過趙盾,只是對君主失信;他若執行君命殺了趙盾,反而是不忠。可見春秋時期的「忠」,不是忠於個人(君上),而是忠於原則(仁道)。所以「忠」是對己,「信」才是對人(君上、朋友)。「忠臣」是「以忠事君」之臣,而不是「忠於君」之臣。中國人看重的「忠」,首先是忠於自己的道德信念;中國人看重的「信」,也不是對他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小信」,而是儒者內心對自己基於仁道而許下之志願(即所謂「初衷」或「初心」);「小信」只是與人約定的表面文章,「大信」才是生死以之的「道」。鉏麑選擇「忠」,然後為其「不信」(不守小信)而死,實際上是全其「大信」。因此,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諒」者「信」也,就是主張堅守正道而不顧小信;甚至孔子還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孟子解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離婁下〉)為了「義之所在」,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果只為對人守信,而做不義之事、造成不義之果,那麼這人仍然是「硜硜然,小人哉」。
事實上,國際法也承認「情勢變遷」原則(rebus sic stantibus),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於1969年通過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62條更明確規定「情況之基本改變」(fundament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可做為終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條約的理由。但此一原則只適用於客觀「情勢/情況」的改變,而不適用於主觀「立場」的改變。36換言之,就「立場」而言,情勢變遷原則並非「禁反言」原則的例外,實際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仍然反對任何國家無原則的改變立場。37
所以,我們若嚴格依據字義,周總理當年所言也不能用來反對中國現在支持琉球民族自決。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當年為何那樣說?放回當年的處境,他那篇講話的背後是「忠」於什麼價值理念?而那個價值是否值得堅持?如果值得堅持,那麼此「忠」不改,就是「唯義所在」,也就是「大信不約」的真意了。然後,我們必須強調:當年中國反對美國從日本手中私相授受接管琉球,是為了琉球的和平、東亞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現在中國基於同樣的價值立場支持琉球脫離日美雙重殖民,豈非「情勢變遷」原則下,中國唯一的正道、君子真正的大信不約?!
說到底,21世紀的東亞,還應該是那個日本霸凌琉球國兩百六十三年,就「有權」把琉球任意「廢國置藩」、再「廢藩置縣」的時代嗎?當今的天下,還應該是美日強權可以任意界定其他國家「邦土」範圍,想「出兵」就打的叢林世界嗎?
不,絕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