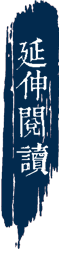臺灣的人造「天然獨」開始批量生產,始於1997年8月出版的《認識臺灣》教科書(於該年秋天起在國中一年級講授)。在其《歷史篇》中,以1600年為界,對此前中國典籍上涉及臺灣的記載皆不視為信史,於是臺灣的「歷史時代」(所謂「有文字的時代」)只剩下四百餘年,而17世紀前的臺灣就成為「史前時代」。並且,從1600年至1662年鄭成功「進取」臺灣(與後面「甲午戰後,日本『取得』臺灣」語意相同)、驅逐荷蘭人為止,被稱為「國際競爭時期」,此一用語強調臺灣並非「中國固有領土」,而且課文將「漢人和日本人」並列為最早進入臺澎的「國際」勢力,意味著日本後來對臺灣進行殖民統治有其歷史淵源。在「國際競爭時期」中,課文還特別突出荷蘭人據臺:「荷蘭人……在1624年8月撤離澎湖,……轉往當時尚非明朝版圖的大員,臺灣本島首次被歐洲人所占領。由此可見,到了十七世紀初,臺灣的國際地位變得更為重要。」雖然課文也說:「臺灣在荷據時代,漢人受到嚴重的壓迫,終於在1652年爆發郭懷一抗荷事件,被殺的漢人達數千人。」但是,這只是「臺灣的國際地位」上升的「代價」,何足掛齒?於是,在這種自賤史觀下,民進黨當局熱烈慶祝「1624年荷蘭人抵達臺南安平,成為臺灣走進世界舞臺起點,臺南市政府在2024年推動『臺南400』,……熱鬧一整年。」1在這一整年的「慶祝」活動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是4月28日臺南市「鄭成功祖廟」舉行的春祭,由民進黨當局的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擔任主祭,不僅邀請當年被鄭成功驅逐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臺灣末代總督的第14代後裔與其家族成員出席,甚至還以鄭成功出生在日本平戶為由,把平戶市長也邀來參加!鄭文燦表示:「多元族群的臺灣後代團結打拚,才有今日的臺灣成就」!2
中國人深知「落後就會挨打」,而臺獨卻相信「挨(外國人)打最光榮」。在這種變態心理下,趁著今(2024)年是1874年日本侵臺的「牡丹社事件」150週年,在當年石門戰役的5月22日這天,民進黨籍的屏東縣長周春米便邀來了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和美國在臺協會的代表、宮古島市的官員,與當年被日軍「討伐」的高士佛社、牡丹社原住民共同「紀念」這場日軍打敗「生蕃」、殺死牡丹社頭目父子的戰役,並一起為「macacukes石門古戰場」3縣定史蹟碑揭牌。周春米表示:一百五十年前的牡丹社事件是「屏東與世界連結重要的歷史節點」,彼此後代子孫學會如何去相互理解與包容,共同守護愛與和平,「誠實面對歷史,了解事件真相,擁抱與接納彼此,才能繼續往前走」。4但是,發生在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稱為「臺灣出兵」,見下圖)實際上是日本以琉球漂民於1871年在臺遇害(八瑤灣事件)為藉口,試圖以武力逼迫中國承認琉球屬日、同時試探殖民臺灣的可能性的一樁侵略行為。5當時,八瑤灣事件並未傷及中琉友好關係,反而日本藉機侵臺才嚴重威脅中日關係,還導致琉球國向日本提出抗議。現在臺獨把當年介於「屬於中國的臺灣府」和「不屬於日本的琉球王國」之間的八瑤灣事件,硬掰成「不屬於中國的『臺灣國』」和「屬於日本的『沖繩縣』」之間的舊有矛盾,然後拉著當年聯手入侵中國臺灣府的日美兩國代表去跟臺灣與琉球的原住民表演「大和解」,這不但是拿臺灣及琉球的原住民當政治工具,辱其尊嚴,也是在日本從1874年起長期侵略中國及其屬國而造成的中日歷史傷痕上再劃一刀,增加仇恨。如此「紀念」牡丹社事件(廣義,包括八瑤灣事件),藏在周縣長那一串漂亮空話背後之真實目的,顯然是要臺、琉、日、美「擁抱與接納彼此」,然後共同對抗中國。
當然,與「臺南400」一樣,屏東「牡丹社事件150週年」紀念活動,也會一直「熱鬧」到年底。

那麼,真實的牡丹社事件究竟有何歷史意義?我們從中應吸取什麼教訓?由於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起手式、從內部顛覆整個東亞地區傳統秩序的第一步,更是日寇併吞琉球、侵略中國的第一仗,因此我們還須從日本的「脫亞入歐」和「琉球處分」談起,然後才能理清「臺灣出兵」及《北京專條》的真相,進而探索確保臺灣及久懸未決的琉球地位問題的解決之道。
吃裡扒外的「脫亞入歐」
自古以來,倭國日本就是威脅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內部禍源。大陸學者馮天瑜、任放指出兩個深植於日本人的文化DNA裡的原因:其一,日本人自認為是「神國」,並把天皇當成「現人神」(以人的型態出現的神)來無限崇拜。馮、任二人指出,「『神國』是籠罩日本人的集體理念,其說脫胎於神道。《古事記》《日本書紀》等神道元典將日本尊為『天神創造之國』(神國),日本人是『天孫之後裔』;天皇是神性與人性兼備的『現人神』,擁有『萬世一系』皇統,是日本國家及國民的象徵;天皇權威自然天成、毋庸置疑,必須無條件遵從。……這一套『元歷史』(民族起源)說教,蘊藏著種族優越論、日本中心論、天皇神聖論、世界一統論(『八紘一宇』),在國家戰略層面必然產生突破島國面積狹小、資源貧乏局限,向外拓展生存空間的擴張性追求。在『神國意識』統轄下,……容易催生極端民族主義和侵略有理論。日本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屢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便是其表現。」6所以,在日本人眼中,全世界的「非日本人」在「品種」上都矮他們一大截,而「神國」日本天生有權利侵略擴張,直到統治全世界(八紘一宇),把所有的「非日本人」都當作工具或資源來役使、甚至屠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七三一」細菌戰部隊裡,日本人把那些被他們拿來進行各種慘絕人寰的活體試驗的中國人(以及其他的「非日本人」)稱為「丸太」(まるた,即中文的原木或圓木),這不只是為了保密,而是他們真的只把這些活人視為可以任意砍削切割的「原木」!
其二,日本人還乾脆否定了道德、良心,以及中國人最看重的「義利之辨」。馮天瑜、任放寫道:「日本人始終明確地否認,德行包含同惡進行鬥爭。正如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們幾百年來所不斷闡述的,認為這種道德律不適合於日本。他們宣布,這正證明日本人道德的優越。日本近代的宗教家及國家主義者宣稱:『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資依賴,沒有必要與自己性惡的一半進行鬥爭,只需要洗淨心靈的窗口,使自己的舉止適合各種場合。』」此即日本「恥感文化」的根源。但是,「日本道德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傷),不一定在『恥感文化』,而在缺失善惡對立的價值觀。加之日本有『死者即佛』『死者成神』的觀念,凡戰死者即為佛為神,故神社供奉『戰犯』順理成章。……因為失卻求善去惡的心靈追求,沒有直逼靈魂的尖銳人生拷問,沒有富於批判精神的終極倫理關懷,所以日本稀缺培育向善思想的歷史文化土壤,而盛產謀略型的思想者。這些思想者……缺乏理性的、善性的形上學指導,往往偏執於民族私利而劍走偏鋒(如吉田松陰『失之美英俄的利益當向中國朝鮮求得補償』的強盜邏輯),擴張與暴力成為他們的主題詞。當此類思想被統治者放大為國民意識時,日本的對外侵略就獲得了強有力的文化支撐,於是世人便見到,一個文雅、潔淨、愛美的民族那樣狂熱地奔向掠奪與殺戮。」7
由於毫無道德負擔,日本人便僅以強弱勝負論斷得失,而不在意是非對錯。人與人之間,強者可恃強凌弱,弱者只能逆來順受。直白地講,日本人只把人分兩類:強者為禽獸(獵食者、predator),弱者為畜牲(獵物、prey),其間並無善惡之分。8世間之事,凡對「神國」日本有利者皆善,不利者皆惡。在這種心態下,日本人若處在獵食者的位置,就可以對獵物做任何事而不會「良心不安」;反之,一旦處在獵物的位置,那又會表現得非常馴良,以避免被害。日本人表現為前者(獵食者/禽獸)的最佳例子,就是日軍在戰爭中對平民及戰俘的殘酷暴行。日本一位小學老師松岡環,因為發現絕大多數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於是花了多年時間尋訪曾經參與大屠殺的前日軍士兵,竭盡可能問出實情,然後整理成書。她在其書《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12月)〈中文版前言〉中寫道:「多數原士兵沒有侵略戰爭的意識,以無反省的語言講述著南京戰的經歷。」「在日本兵的證言中,關於日常化地殺害中國民眾、捕捉女性強姦,是以無所謂的口氣(輕鬆的心情)講述的。」2016年「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之前,松岡環在大連舉辦了一場名為「正視歷史」的講座,她說:「在我能找到的250個日本兵裡,對戰爭有反省的不超過4人。」9以這樣的樣本母體計算,日本人中只有1.6%是有「良心」的!至於日本人表現出「獵物/畜牲」的例子,則是在太平洋戰爭中經常令美國人訝異的:一個日本兵可以在發起兇猛的自殺式「萬歲衝鋒」之後,若未死而被俘,立即變得極其溫馴,判若兩人。當美軍進占日本後,發現連裕仁天皇都服從性極高,竟主動拜訪麥克阿瑟。但是,同一個裕仁,卻剛剛在1945年8月15日廣播的《終戰詔書》中與他的大臣用盡機巧,埋下了未來賴掉戰罪、重寫歷史、捲土重來的一切必要伏筆!10「天皇」果然是大和民族的代表,從裕仁的表現,可以看出日本的民族性:即使戰敗,仍無道德反省;即使淪為畜牲,仍然機關算盡,試圖翻身再為禽獸。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中國人致力於保存「異於禽獸者」尚且不及,很難理解世上竟有一個大和民族直截了當地以當禽獸為目標——而且要當食物鏈最頂端的那一種禽獸,以免淪為畜牲。但正因為日本對自己在「食物鏈」上的位置非常敏感,所以面對1853年「黑船」叩關11的衝擊,整個日本幾乎是以動物性的本能很快啟動了有效反應——從倒幕運動,直至明治維新。12
正由於日本的許多維新作為,幾乎是基於自身傳統文化基因的本能而動,是「實際先行」而非「理論先行」,所以往往一開始的表述較為含糊,後來才陸續總結出幾個大原則,但是總體方向從來沒有變過。13例如,維新伊始,1868年4月6日(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宣布了「五條御誓文」,其中第五條是「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乍看之下,彷彿只是個好學的誓言,人畜無害。但是在同一天,明治又發表一封御筆信「宸翰」,向國民宣布:「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嶽(按:即富士山)之安。」日本人一聽就懂——這是要朝向「國際食物鏈」的上端移動了。
由於日本人以獵食性動物視角觀看世界,因此他們先天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信徒,認為國際政治理應遵循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那麼,若要「布國威於四方」,首先就必須擺脫其他亞洲國家的「獵物」地位,爭取成為與西方列強並肩的「獵食者」,於是他們開始「脫亞入歐」。而如馮天瑜、任放所言,「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存在一個『脫亞』—『興亞』的悖論:一方面,日本努力效法西方,拼命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試圖『脫亞入歐』、全面西化,讓西方世界承認日本為東方唯一強國,接納自己進入帝國主義瓜分盛宴。另一方面,面對西方列強奴役亞洲的態勢,日本作為亞洲新興強國,期待將西方勢力驅趕出亞洲,由日本獨霸之。因此,日本宣稱自己是『興亞』的盟主,所發動的一系列戰爭是『聖戰』,是『自存自衛』『解放亞洲』『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正義之戰』。」14
換言之,日本的「脫亞入歐」,不是「靠向歐洲」,而是先學習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然後獨霸亞洲、奴役鄰邦、排除歐美,最終完成「八紘一宇」。那麼,他的首要目標,自然是從亞洲內部裂解由中國引領的「天下秩序」(即宗藩體制),使自己「脫穎而出」,躋升列強之一。所以,它的矛頭首先對準中國,於是在1871年與中國簽訂表面平等、其實暗藏玄機的《中日修好條規》(日方稱為《日清修好條規》)。
不懷好意的「日清修好」
日本一方面要爭取在國際法上與西方列強地位平等,另一方面又要學西方國家以國際法為武器,蠶食中國、裂解「天下」,於是1870年9月即派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到中國要求訂約。總理衙門(亦稱總署)起初以「大信不約」婉詞謝絕,僅允許照常通商。柳原深知中國人心理,便對李鴻章說:「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此語正中李鴻章「以夷制夷」之下懷,李於是上書總理衙門,贊成與日本訂約,總署便於10月31日回覆同意,惟俟日方特派大臣到天津再議。15日本即於1871年6月11日任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全權大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率領使團派赴中國議約,中方則由李鴻章領軍。日使團於7月21日到天津,25日與李鴻章開始會談,9月13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日方稱為《日清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條規》還沒生效,日本就想改約,但中方拒絕,最後才在1873年4月30日互換批准書而生效。16
此約在談判時,日方一開始就想援引西方國家之例,把種種不平等的特權訂入條約,中方堅持不允,後來日本要求改約仍是欲使其成為片面立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中方仍拒絕。但是,中方沒有警覺到傳統的宗藩體制與西方國際法無法並存,總想在東亞地區維持傳統秩序,並且習慣以傳統觀念理解條約用語,這就讓日本有了引用西方國際法學說來藉機生事的可能。首先,中方為了將對日關係(當時在中國眼中,東亞地區屬於傳統「天下」秩序的範疇)和對西方國家關係區別開來,便將「條約」改為「條規」,並反對將日本「天皇」稱號寫入,實際上此二者在西方國際法上皆無關宏旨。反之,日方則反對中方使用「中國」一詞,認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稱「大清國」。對此,中方認為「中國」是與「大清」對等、對外亦可使用的國號,17不能改變。最後雙方商定條約起首處以「大清國」和「大日本國」並稱,而中文文本內條文則由中方決定。結果,中文版在第六條仍自稱「中國」。但是,透過這些爭執,日本成功地使中國將注意力集中在爭「天朝」的體面,而忽略了條約文字可能有的實質漏洞。此外,因中國飽受賦予西方國家「片面最惠國待遇」之苦,故堅持在此約中不寫入「一體均霑」,但是雙方在對方疆域內皆享有領事(參與)裁判權,18可見中方雖知「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在於「片面」造成的不平等,但外國領事參與司法裁判則違反了國際法上「領土」的排他性,易致爭端。
至於該條規文字的最大漏洞,在第一條:「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問題就出在雙方對「邦土」一詞的理解自始不同。中方對「邦土」的理解,包含了版圖內的「化外」地區(如臺灣的「生番」地區19)及藩屬國(琉球、朝鮮等),但日本則以嚴格的「有效控制」來定其範圍,以至於不僅琉球、朝鮮等藩屬不在其內,連臺灣「生番」地區的主權也可挑釁。這個爭執,在修約時隱而不顯,但是在約成之後日本禁錮琉球、進犯臺灣、覬覦朝鮮時,則不斷出現。直到牡丹社事件之後,琉球已被日本禁止入貢中國,日本一方面要中國出面要求朝鮮對日開國通商,另一方面又不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於是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等人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於1876年2月14日發生了以下交鋒:「森大臣(按:即森有禮)云:高麗與印度同在亞細亞,不算中國屬國。[李鴻章]答云:高麗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森大臣云:各國都說高麗不過朝貢受冊,[中國]不收其錢糧,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屬國。答云:高麗屬國幾千年,何人不知。和約上所說所屬邦土,土字指中國各直省,此是內地,為內屬,征錢糧,管政事;邦字指高麗諸國,此是外藩,為外屬,錢糧、政事向歸本國經理,歷來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說不算屬國?」「鄭署使(按:鄭永寧,生長於日本,為鄭芝龍後裔)云:森大人因總署說中國不管高麗內政,所以疑不是屬國。答云:條約明言所屬邦土,若不指高麗,尚指那〔哪〕國?總署說的不錯。森大臣云:條約雖有所屬邦土字樣,但語涉含混,未曾載明高麗是屬邦,日本臣民皆謂指中國十八省而言,不謂高麗亦在所屬之內。答云:將來修約時,邦土句下,可添寫十八省及高麗、琉球字樣。」20中日雙方就這樣在會議桌上各說各話,但是日本則一直在戰場上「憑實力說話」,步步進逼,中國則節節敗退。
事後回看歷史,日本對中國(及其屬國)從來就不存「修好」之心,該條規只是其將中日關係由天下秩序拖進西方國際公法體制、以便日本逐步侵吞的法律工具。於是雖然《日清修好條規》於1873年生效,也無法阻止日本於翌年入侵臺灣、1879年併吞琉球。隨著日本國力上升,1894年7月16日與英國締結了雙方平等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日本終於掙脫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成功「脫亞」。但是九天後,日本就在7月25日挑起甲午戰爭,開始了稱霸亞洲的關鍵步驟——擊敗中國。大陸學者韓東育指出:「日本能與西方列強取得對等地位,顯然更多得益於《中日修好條規》及其所埋下的伏筆。這意味著,琉球問題、朝鮮問題和臺灣『番境』問題,說到底,不過是一個問題而已。近代以來日本的膨脹及其系列行動,終於使虛實參半的『華夷秩序圈』被徹底解構;而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亦終於在東亞地區變成了不爭的現實。」21
恃強凌弱的「琉球處分」
前已言之,日本在與中國商談《修好條規》時,便預布了染指琉球、臺灣、朝鮮的伏筆。前二者又被日本併吞琉球的所謂「琉球處分」中的「臺灣出兵/牡丹社事件」牽扯在一起。那麼,「琉球處分」是什麼?日本究竟有沒有權利「處分」琉球?
根據日本編撰的歷史百科全書《國史大辭典》,所謂「琉球處分」是指「明治政府切斷琉球與清國的朝貢關係的綜合措施」。22但是,如果只需要「切斷中琉關係」,琉球就完全屬於日本,那麼其隱含的前提就是:琉球本來就屬於日本,只是與中國維持著「不合法」的朝貢關係而已。然而這個前提完全是倭寇「強盜邏輯」的產物,因為琉球長期為中國的藩屬國,而日本對琉球的所有「權利」皆為武力脅迫而來,並非正當合法。日本將其對琉球國由1872年「廢國置藩」至1879年「廢藩置縣」的一系列侵略行為統稱為「處分」,語意上就成為實施日本的「規則」或「法律」的過程,於是非法變為「合法」。因此,所謂「琉球處分」的正確表述應為日本「非法吞併琉球」。23
事實上,在日本1872年開始進行「琉球處分」之前五百年的1372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遣使招撫琉球,琉球的中山國王察度即派遣其弟跟隨明使入朝進貢。從此直到1879年日本併吞琉球,中琉之間維持了五百餘年的友好宗藩關係。此期間,中國共冊封琉球國王二十三次,派遣正副使四十三名,琉球對中國則從三年兩貢到兩年一貢,垂為定制。琉球不但因接受中華文化而成為「守禮之邦」,並因參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而成為「萬國津梁」。誠如2023年6月1日習近平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時所言:「我在福州工作的時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淵源很深,當時還有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
然而,在琉球成為中國藩屬兩百三十七年後的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薩摩藩為了壟斷日琉貿易(實即間接對華貿易),派兵入侵琉球王國,將其君臣擄回薩摩,前後拘禁兩年五個月之久,直到1611年琉球國王及大臣們被迫宣誓效忠薩摩藩,才被釋回(拒降的三司官鄭迵則被日人烹死)。從此,琉球就處在日本薩摩藩的實質控制下。因此,琉球對日本的所謂「臣屬」關係,是在其與中國建立起基於自願的朝貢關係之後兩百多年,由日本以武力威逼而成。薩摩藩因垂涎與中國貿易之利,便刻意對中國隱藏其逼迫琉球臣屬的事實,使琉球繼續與中國維持常態封貢關係,如此薩摩藩即使在德川幕府於1633年頒布鎖國令後,仍可經由琉球獲得對華貿易之利。這就是日本所稱的「兩屬」狀態。姑不論琉球向薩摩藩稱臣本非自願,僅就薩摩長期隱瞞其挾持琉球的實況而論,因武力強迫而成的「兩屬」關係當然非法。
這種偷偷摸摸的非法「兩屬」狀態持續了兩百五十多年後,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薩摩藩既參與擁立明治天皇的倒幕運動而有功,便想趁勢將其對琉球的非法掌控化暗為明,於是薩摩藩24於1871年8月27日(廢藩置縣前兩天)向外務省提出《鹿兒島藩琉球國事由取調書》(鹿兒島藩關於琉球國事務調查書),要求收回「古史記載屬於日本皇國」的「沖繩島」。於是,日本開始謀劃「琉球處分」。但是,正由於該「處分」本屬非法,因此日本需要找到合適的藉口。
正好此時發生了「八瑤灣漂民事件」。1871年,從琉球宮古島去首里王城進貢的船隻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風雨,12月17日(一說19日)25漂到臺灣東南部的八瑤灣,六十六人登岸。隨後,他們誤入排灣族原住民的高士佛社,並在試圖逃離時被原住民追殺。結果五十四人不幸身首異處,僅有十二人被漢人楊友旺救下,送往鳳山縣衙轉送臺灣府(今臺南)安頓,後被送往福州,給予補給後搭乘返程的船隻於1872年7月12日回到琉球那霸港。關於八瑤灣事件,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一、琉球學者平良勝保指出:當時琉球人知道「救助東亞海域的漂流民並將之送還到其母國的制度(國際法)還發揮著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地區不在此範圍內,比如臺灣(按:指「生番」地區)。」而且,「琉球人本身,在面對『異體之人』(按:指文化習俗差異很大者)帶來的危機時,也並非總是保有善意。」因此,根據宮古島的文獻紀錄與遇難倖存者的講述來看,琉球方面對此事件的認識是遭遇了「事故」,而非「被害者」。26所以琉球國王對中方依慣例(相當於國際習慣法)處理此事不但毫無異議,還表示感謝(後詳)。
二、中方的福州將軍文煜亦於1872年4月2日向清廷奏報此事:「臣等查琉球國世守外藩,甚為恭順,該夷人等在洋遭風,並有同伴被生番殺害多人,情殊可憫,……生番見人嗜殺,殊形化外,現飭臺灣鎮、道、府認真查辦,以儆強暴而示懷柔。」清廷則諭令文煜等人:「飭該鎮道等認真查辦,以示懷柔。」可見中國政府雖將「生番」視為「化外」,但未自認對「化外」之民無管轄權;即使「查辦」未能落實,也只是執行的問題,而非有無管轄權的問題。
三、琉球國方面不但對中方照護倖存者表示感謝,在得知日本欲藉機生事、出兵犯臺後,琉球王府在1872年10月5日還發表聲明反對「臺灣出兵」,以免影響中琉關係。27可見日方藉口琉球國王要求日本代為「討伐」臺灣,完全是無恥謊言!28
如前所述,日本從八瑤灣事件前不久,已決心為切斷中琉關係尋找動手的藉口。而根據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確定:日本以此事件為藉口出兵犯臺,純粹是基於自己的侵略動機,將一件與日本無關的琉球船難事件,扭曲利用來發動一場琉球反對的不義之戰!誠如平良勝保所言:「無論從當時的東亞國際秩序(按:即宗藩體制)來看,還是基於『萬國公法』的倫理角度而言,臺灣出兵都是無視作為國際社會一員而存在的『琉球國』的意志的行為。其背後,是不斷暗示合併琉球國……的壓力在發揮作用。」29換言之,這是藉著侵犯中國來併吞琉球國的雙重侵略惡行!
那麼,決定「臺灣出兵」前,日本又是如何知道八瑤灣事件的?
就在該事件同(1871)年9月13日,中日簽署了《中日修好條規》。但在條約尚未生效前,日本又派外務大丞柳原前光於1872年5月6日到天津要求改約,正好在京城邸報上看到了前述的文煜奏摺,得知琉球人在臺灣被「生番」殺害,便將該奏摺抄寄外務卿副島種臣。同年7月5日,日本大藏大輔井上馨便提出併吞琉球之議,認為琉球「奉中國正朔,接受中國冊封」,而日本一直未「匡正其攜貳之罪」,現在在明治維新的新形勢下,應「清除從前歸屬不明之積弊」,「招彼之酋長至宮闕之下,責其不臣之罪」,而後「速收其版籍,明確歸我所轄」。恰恰稍後不久,日本駐琉球的代表在當地得知琉球漂民被中方送回來的經歷,於7月間向鹿兒島縣(原薩摩藩)參事大山綱良報告,大山見獵心喜,便於8月31日上書明治政府請求「興問罪之師」,以武力「上伸皇威於海外,下慰島民之冤魂」。
日本以上說詞中,將1609年日本薩摩藩侵略琉球視為琉球長期屬日的歷史起點,而琉球對中國起始更早、基於自願的朝貢,反倒成了「攜貳之罪」!日本只需要切斷中琉之間的朝貢/冊封關係,即可「變非法為合法」,完全併吞琉球,這就是強盜邏輯!於是,日本政府綜合大山綱良及井上馨的算計,前後長達七年的「琉球處分」就此展開。
日本動作極快,當即走出第一步——「廢國置藩」。1872年10月15日,就在琉球正使伊江王子尚健等人覲見明治天皇之時,天皇當場下詔「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列入華族(即貴族),隨後又發布命令,將琉球與各國締結條約及對外交涉事務都收歸日本外務省管轄。但是,琉球朝貢了五百年的宗主國中國如果不予認可,那麼日本突襲式「冊封」琉球就無法「合法化」。然而,正由於薩琉關係隱瞞中國兩百六十餘年,現在日本若突然宣稱替「屬國」琉球向臺灣「興師問罪」,也實在吃相難看。於是,日本還需要更多的「藉口」。
1873年初,日本本州小田縣船戶佐藤利八等四人也在海上遇到暴風,漂流五十餘日後,於3月8日到達臺灣東南岸的馬武窟,登岸後亦遭到當地原住民奪取財物,但被地方首領陳安生帶回家保護,未被殺害。後來陳安生將四位日本漂民送往鳳山縣,再一路由中國地方官送至福建通商總局,最後送交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為此,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品川忠道還致函蘇松太道沈秉成道謝,謝禮並託沈轉交救護日本漂民的中國人。與此同時,由於不少外文報紙報導了日本欲借琉球漂民被殺一案生事,閩浙總督李鶴年於1873年5月30日致函總理衙門,詳細敘述事件經過,並提到「據琉球貢使向德裕等稟稱:奉該國王面諭,島袋等十二人(按:即獲救之琉球人)蒙恩救出,現已回國,曷勝感激,謹備銀三百元,請轉給楊友旺等以為酬勞等因到閩。現據署臺灣道夏獻綸詳稱,牡丹社生番戕殺琉球人一案,已遵旨派委前臺防同知游熙等前往查辦等情。鶴年等查生番圍殺琉球難民,情殊可惡,自應認真查辦,以警凶頑。琉球國王感激懷柔之德,甚至奉銀酬謝,其必不別生枝節可想而知。現聞日本使臣將借琉民被害一案向貴署饒舌,……用敢先敘原委奉達,以備杜其藉口。」可見中國地方官對「化外」之民並未置之不理,而且琉球國王都已對中方救助琉球漂民表示謝意,兩地之間全無未解紛爭。到此為止,照理說這兩件事都應該圓滿結束。然而,當禽獸看中了眼前的獵物,怎有可能輕易放過?結果這兩案都被日本歪曲事實,一併作為出兵犯臺的藉口。
不過,為了確定此役不至於擴大到失控(包括避免西方列強干預),日本還需要「合理化」其籌畫已久的「臺灣出兵」的說詞。因此,1873年6月21日日使柳原前光、鄭永寧等來到總署會晤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質問琉球人被殺事件。黃遵憲依據中方史料記載:「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夫二島(按:指琉球與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蕃者何?』曰:『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貴國捨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為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覆論詰者累日,卒不能畢議。及前光歸,白狀,於是征臺之議遂決。」30在此,柳原「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固屬強詞奪理,「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則是堂堂一國使節而作偽證。但是,中方官員尚未警覺到日方是依據「有效控制」來定義「邦土」,因此中方既未力爭琉球絕非日本「版圖」,也未強調中國政府對「化外」之地雖「未便窮治」但仍有主權(管轄權)。而且,由於中方官僚系統情報不通暢,既不知琉球王府已抗議日本以八瑤灣事件做出兵藉口,也無法當場拆穿日使偽證「小田縣民遇害」,使得此次交鋒中方底氣不足,留下模糊空間讓日本作文章。事後看來,日本的陰險狡詐,已十足展現。
於是,一場既無視琉球國的存在,也違反《中日修好條規》的「臺灣出兵」,在日寇謊話連篇的狡辯之下,已然箭在弦上。
以怨報德的「臺灣出兵」
在柳原前光、鄭永寧等與毛昶熙、董恂交涉日方捏造的「臺灣原住民殺害日本國屬民」時,日本使臣副島種臣正在爭取覲見同治皇帝時不下跪磕頭、僅行鞠躬禮。後來中方退讓,副島遂其目的,而後日方態度放軟,使得總署與李鴻章都以為日方只是用八瑤灣事件和「小田縣民遇害」做談判籌碼,在覲見禮節問題解決後便「自為轉圜之計」。於是,中方「把日本想得太好了」,錯判了日本的真實意圖,以致對日本興兵犯臺毫無準備。
1874年2月6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和參議大隈重信擬定《臺灣蕃地征伐要略》(未公布,以下簡稱《要略》)31,第一條就是將「臺灣土蕃部落」視為「無主之地」,於是,「報復殺害我藩屬琉球人民之罪,為日本帝國政府之義務,而征蕃之公理,亦可於此中獲得主要根據。」這就是把清廷基於傳統尊重原住民自治而「未便窮治」之地直接視為無主之地,隨之便可依國際法「先占」原則取得其主權。且日本以「報復殺害我藩屬琉球人民之罪」為「征蕃」之口實,就是要確認琉球屬日。但是,日本又無法否認琉球長期與中國間之封貢關係,於是日本在講不出「公理」時,就赤裸裸「用實力說話」,於第三條規定:若中方提出「兩屬」之說(這本是日方的主張),則「遑顧不理,不應酬其議論為佳。蓋控制琉球之實權,皆在我帝國,阻止琉球遣使納貢之非禮,可列為征伐臺灣以後之任務,目前不可與清政府徒事辯論。」這一條恰好反過來證明琉球原來一直對中國遣使納貢。這就是日本的強盜嘴臉,不僅惡用國際法(利用「邦土」之不同定義)為其侵略張目,當國際法也說不通時,就直接訴諸實力,乾脆不講理。此外,這個《要略》還有一個用心極險惡的條文,即第六條:「(負責交涉的)領事不管蕃地征撫之事;負責征撫事項者,不管交涉之事。」意思就是要邊談邊打,以戰場上的威逼來迫使中方在談判桌上讓步。這導致中方在後來的談判中很難確定日方代表答應的條件是否能約束日本軍隊,於是壓力倍增。日本這一陰毒手法,後來在甲午戰爭中的馬關談判裡又完整地重演了一次。
《要略》在內閣會議通過後,大隈重信被任命為「臺灣蕃地事務局長官」,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則為「臺灣蕃地事務都督」,率兵犯臺;柳原前光為駐華公使,福島九成為駐廈門領事,負責外交交涉。321874年5月2日,先遣部隊出發,5月7日登陸臺灣南部射寮,5月22日於石門隘口擊敗了原住民。6月初日軍分三路攻擊牡丹社及高士佛社,並焚毀攻下之部落。至7月中旬,戰事基本結束,日軍退回沿岸駐守。但是,日軍很難適應臺島氣候,病歿者多於戰死者。據日方統計,此役前後歷時7個月,日方動用兵力3658人,戰死12人,而病死者高達561人,是前者的47倍。33當時隨軍軍醫落合泰藏詳細寫下在臺日軍的慘狀:「參加這次生蕃討伐之役的士兵,所嘗到的艱難辛苦,究非筆墨所能詳述。在這南海絕島瘴癘之地,時常有連宵暴雨。所有溪流,到處濁水滔滔,一片汪洋。……又有粗暴的颶風,不時襲來,不分山河,都被吹刮得淒淒慘慘,當時設備不全的營房,很易被刮倒,簡直躲避無地。……糧食本不完備,又加上運輸困難,常為泥路及險惡的斜坡所阻,戰鬥部隊……有時,只能靠已經腐爛發著惡臭的飯糰充飢。……全軍都患瘧疾,苦悶呻吟之聲,慘不忍問。……處境艱苦,完全和流放一樣。」「從6月下旬起,病人普遍地增加,至7月中旬,形勢非常猛烈,終至醫院的職員、醫師、藥劑師無不為病魔所困。8月後,[野戰醫院]一個健康的人也沒有了。……到9月4日,一切方法,都已想盡,只能向都督(按:即西鄉從道)提出意見書了。」事實上,早在六月底左右,「征臺軍大多患病,處境慘痛的情況,已上達天聽。」34長期研究此一事件的牡丹社原住民高加馨寫道:「最後統計參加戰役的軍人(3658人)及軍中文職人員總共約5900人,病人人次是16409人次,多於兵員總數是因為有人罹病2-3次,最多一日有600名病患之多,連醫官本身都病倒。……可見得如果戰事繼續下去,勝負還在未定之數,日軍不用和原住民作戰,可能就先被惡劣的氣候與不適應的環境給打敗了。」35原本以為可以「伸皇威於海外」的臺灣出兵,竟然落到如此窘困的境地。為了使已成雞肋的臺灣出兵能夠體面結束,日皇明治不得不於8月5日再加派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赴中國辦理臺事交涉。
反觀清廷方面,總理衙門直到1874年4月18日才從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處得知日本即將出兵侵臺。恭親王奕訢在接到英使信函後,於5月14日上奏稱:威妥瑪據英國駐日使館電報,「知日本運兵赴臺灣沿海迆東地方,有事生番;並詢及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隸入中國版圖;東洋興師,曾向中國商議准行與否……。當經臣衙門函覆該使,答以上年日本國使臣往京時,從未議及有派兵赴臺灣生番地方之舉。……臺灣生番地方,係隸中國版圖,且中國類此地方,不一而足,未能強繩以法律。……臣等伏查上年四月間,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來京,曾派其隨員柳原前光、繙譯官鄭永甯來臣衙門,向臣等面詢……臺灣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擬遣人赴生番處說話等語。當時即經臣等面為剖辯。該隨員等未經深論,臣等亦未便詰其意將何為。……臣等送該使臣回國時,復告以嗣後總當按照修好條規所載,凡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該使答曰,固所願也。是該國並未與中國議及派兵前赴臺灣。刻下忽有此舉,揆之各國往來之理,似不應出此。」36奕訢不敢欺君,其所言日方事前「從未議及有派兵赴臺灣生番地方之舉」及「該國並未與中國議及派兵前赴臺灣」應屬可信。我們由其奏摺還可看出:中方也始終將「生番」之地視為「邦土」,從未放棄管轄權。只因中國向來與人為善,以和為貴,因此從中方觀點看來,琉球國王既已為中方救護八瑤灣事件倖存者而致謝,日方也為佐藤利八等四人獲救而道謝,哪能料到日本這個白眼狼本質的國家竟以怨報德,把兩件事用謊言綁在一起,當做「興問罪之師」的藉口,既挑戰中國對臺灣「生番」地區的主權,亦突顯日本自稱的對琉主權。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日本對中國可謂將此言發揮到淋漓盡致!
日本決定出兵犯臺後,西鄉從道於4月13日寫了通知閩浙總督李鶴年的照會,但卻是交由隨兵船出征的陸軍參謀兼駐廈門領事福島九成隨身攜帶,於5月3日兵船停靠廈門的翌日,才交廈門海防同知李鐘霖代轉。李鶴年收到照會時已是5月8日,而日軍則在前一日就已登陸臺灣射寮。顯然這又是一個日本精心設計的詭計,讓中方在看到日本出兵照會時,就必須面對「日軍已在臺灣島上」的既成事實。37
西鄉從道在照會中寫道:「臺灣土蕃之俗,自古嗜殺行劫,不奉貴國政教,海客菑難是樂。邇年我國人民遭風漂到彼地,多被慘害。……是以我皇上委本中將以深入蕃地,招彼酋長,百般開導,殛其凶首,薄示懲戒,使無再踏前轍,以安良民。」附片中具體指出出兵的理由是:「明治四年十二月,我琉球島人民六十六名遭風壞船,漂到臺灣登岸,是處屬牡丹社,竟被蠻人劫殺,五十四名死之,十二名逃生,經蒙貴國救護送回本土。又於明治六年三月,我備中州人佐藤利八等四名,漂到臺灣卑南蠻地,亦被劫掠,僅脱生命,幸蒙貴國恤典,送交領事,旋已回國。……兹我政府獨怪土蕃幸人之災,肆其劫殺,若置不問,安所底止,是以遣使往攻其心。」38李鶴年回覆:「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番』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為?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我地,勿啟二國釁。」39可見中國地方大員皆知日本出兵不僅違反《中日修好條規》,而且以小田縣民遇禍(但未遇害,而且已獲補償)為詞實屬恩將仇報。但是,中國的海陸軍裝備戰力皆不如人,且當時中國危機四伏,俄占新疆伊犁尚待解決,法國侵吞越南又日趨積極。在日本的「實力」面前,中國只能透過外交途徑解決。
清廷意識到日本犯臺的嚴重性,於是在5月14日即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帶兵赴臺設防,5月21日增派福建布政使潘霨赴臺幫助交涉。當柳原前光於7月31日到北京後,總理衙門即照會柳原:「上(按:1873)年貴國大臣副島遣貴大臣(按:即柳原前光)來本衙門面譚各節,本衙門前次照會貴國外務省,已盡言之,並無許貴國自行查辦之說。……如琉球曾受生番之害,應由琉球國請中國處置。即謂琉球國與貴國素有往來,貴國必欲與聞其事,亦應照會本衙門辦理。至謂貴國人民曾經受害,兩國既有條約,如有其事,尤應言明某年月日、某人在某處、若何被害,照會本衙門查辦。中國無不為查辦之理。萬一中國不為查辦,貴國或以允否自行辦理,詢我中國可也。斷無徑自用兵之理,中國亦無允貴國自行查辦之理。乃並無一、二文件照會本衙門請為辦理,而遽自行查辦,不但查辦,而且突然稱兵入我境內,揆之於理,豈可謂平?……副島大臣於上年來覲時,並未一言及此,本王大臣(按:奕訢)何從異議?即貴大臣來署,向本大臣述及臺灣生番,其時並無派兵前往之說。……本王大臣未嘗許貴國自行查辦。……且上年貴副島大臣在京時,履次晤譚,實未言明臺灣生番之事。……而貴大臣此次照會,內稱貴中將西鄉所辦事宜(按:即帶兵犯臺),與上年貴大臣所言,何嘗不符,是貴大臣自誣也,是貴大臣以自誣者誣本王大臣也。」柳原隨即回覆:「查上年我副島大臣在京議覲事,……特派本大臣至貴衙門代陳臺灣生番之事;是與副島大臣親口相告,原無差別。其時本大臣云,我國屬民,即受生番枉害,必須派差查辦,意在除凶安良,番地不奉貴國政教,畫地自居,我國此行,恐觸貴國嫌疑,故特相告而去等語。夫我國伐一野蠻,本不欲告諸他人之國,然我副島大臣篤念兩國和誼,乃爾相告,則帶兵與不帶,惟我所欲,貴王大臣當時並無細論,又無異議,於我何所再言。況為特防嫌疑而相告,原無請允查辦之意,又何煩文書往來乎?本大臣信不自誣,敢誣貴大臣哉?」40由此公函往來可見:一、中方從未承認日本有權干涉中琉關係,也從未放棄對「生番」地區的管轄權,更從未允許日本「自行查辦」臺灣「生番」;二、日方承認1873年6月21日只提到要對臺灣「生番」「派差查辦」,並未提及出兵,但是日方堅持既然中國對「生番」之地不「強繩以法律」,就屬無主之地,那麼日本「伐一野蠻」、「帶兵與不帶」,皆「惟我所欲」!三、就算按照日本的說詞,「臺灣出兵」與否皆「惟我所欲」,那麼為何在談判中又希望中國賠償日本的「軍費」?說穿了,日本的態度就是「我就當強盜了,你能奈我何?」
由於日本糾著「化外」不放,以此合理化其侵略惡行,清廷便於1874年6月9日發出詔諭:「日本並不遵約回兵,已與生番接仗,並擬即日移營進剿,其蓄謀尋隙,意圖占踞,已可概見。……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41此即日本出兵犯臺後清朝在臺灣推行「開山撫番」的由來,其動機仍是在保護原住民,而非如後來日據時期的「理蕃」著重於經濟開發。42但是,最後使得外交協商奏效的,不是我們擋得住強盜,也不是強盜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如前所述,即強盜在臺灣的日子過不下去了——只有生病的強盜,才是「講理的強盜」。
日本原擬長期在臺駐軍設治,所以設「臺灣蕃地事務局」,西鄉從道則以「臺灣蕃地事務都督」頭銜在臺領軍。《臺灣蕃地征伐要略》第四條還提出:「在空言推託、牽延時日之際,就完成其事,即是不失和好的機靈外交之一法。」於是,先遣來華任駐華公使的柳原前光,在談判時東拉西扯、不斷重複,還明言他與西鄉從道皆有「全權」,因此他在上海或北京所承諾的,未必能約束在臺灣的西鄉。這就是「空言推託、牽延時日」的「機靈外交」。然而,強盜再奸詐狡猾好勇鬥狠,終敵不過「水土不服」。在日軍隨軍軍醫落合泰藏所言「9月4日,一切方法,都已想盡」之後,日本加派的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於9月10日到京,這才使得談判峰迴路轉。43但是,「講理的強盜」還是要錢的。大久保利通原先漫天要價,至少要兩百萬兩銀(洋銀五百萬元)才肯退兵,中方直接拒絕,大久保便以離京回日作要脅,甚至起草了一個照會,作態回到最初的立場(「生蕃」之地不屬於中國)。最後,在英使威妥瑪調停之下(實際上仍是給日方下台階),雙方於1874年10月31日簽訂了《北京專條》,強盜發起的「臺灣出兵」居然和平落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