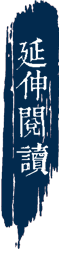第一講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續)
第二節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
自然,我們所說的這一個「知」,不是「妄自尊大」之「知」,也不是「妄自菲薄」之「知」,而是從「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認識」和「自我再認識」之深處所得到的一個「真知」。
說到這裡,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也就因之發生了。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或可說我們的列祖列宗們,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最好說對於我們的「中國之國」,是不是一向是有著正確的自我認識?近百年來,身處於這一個千古未有的歷史變局之中之我們前兩代、前一代和我們這一代的國人,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又是不是有著正確的自我認識?或者是正犯著認識不清、認識不足、甚至嚴重地自我誤認的病症的呢?
要回答這個巨大而切要的問題,自只有從歷史溯起。
中國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古史,尤其是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曾經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古先民、我們的列祖列宗們,對於我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差還能一向地保持著正確的認識,至少是相當正確的認識。因而,他們也一向是懷著強烈的自信和自尊的心境去看待我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
即就嚴格的歷史年代講,中國人把「中」字和「國」字連用在一起,漸次形成為一個具有具體內容的專名辭──「中國」,用以明確地代表並說明一個特殊的、高級的、前進的政治區域、政治生活、政治形式,或文化區域、文化生活、文化形式,或民族區域、民族生活、民族形式,已遠始於兩周之世。然我們仍可得而言者,先「中國」一辭之出現和存在,似已早有一些與「中國」一辭有著同意義或前行者的名詞存在著。例如,意為從野蠻世界逐漸興起之文明世界的「禹跡」、「禹績」和「九有」,以及意識著中居「四方」之「中」或「天下」之「中」的「商方」或「中商」。
我們知道,遠在殷商之前,或可說遠在夏、商之世,以迄兩周之際,當我們的古先民們在當日為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諸蠻族所包圍之東亞大陸的核心──黃河中下流──烈山澤、驅猛獸、開阡陌、治河渠、布五穀、樹桑麻、建宮室、築城廓、造文字、作書契,創造出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之東方型的文化或文明之後,就漸次地開始了「維禹之績」語出《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維:通惟,是。績:業、功。攸:於是。皇:大。辟:君主。烝:美。《鄭箋》:「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諸蠻族所包圍之東亞大陸的核心──黃河中下流──烈山澤、驅猛獸、開阡陌、治河渠、布五穀、樹桑麻、建宮室、築城廓、造文字、作書契,創造出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之東方型的文化或文明之後,就漸次地開始了「維禹之績」語出《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維:通惟,是。績:業、功。攸:於是。皇:大。辟:君主。烝:美。《鄭箋》:「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
「禹績」或寫為「禹跡」,指禹足跡遍及之地,語出《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芒芒禹跡,畫為九州。」芒芒:茫茫,水盛貌。1 、「九有有截」語出《詩經.商頌.長髮》:「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九有:指九州、九域。有截:齊一貌。2 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語出《詩經.商頌.殷武》。翼翼:繁盛豐美貌。《鄭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3 ,以及「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語出《尚書.周書.武成》。蠻、貊:古代稱當時文明發展相對滯後的南方和北方部族。率:遵循。俾:服從。指當時華夏族及周邊部族,沒有不遵服周武王的。4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語出《論語.八佾》。此句歷來因斷句出入,而有解釋的差異。針對本文所採斷句,《正義》曰:「此章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此處,「諸夏」即為共享文明的共同體。5 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進於夷狄,則夷狄之」「進於中國」即「進於文明」,「進於夷狄」即「進於野蠻」。此種以「文明」作為「華夷之辨」的思想,始於孔子。韓愈〈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楊樹達(1885-1956)之《論語疏證》中亦云:「《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蓋孔子於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為準,而以行為為準。」6 之「文明」與「野蠻」的區分的覺識。他們也就自稱我們自己為「禹績」、為「九有」、為「中商」、為「華夏」、為「諸夏」、為「中國」。
這自是說,我們之各該當時的古先民們不但已自覺地覺識到,我們自己之在各該當時已有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的創造和保持,而且還自覺地覺識到,我們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是比各該當時之野蠻的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的多。或可說,他們不但已自覺地覺識到我們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是比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的多。或可說,他們不但已自覺地覺識到我們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是比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而且自覺地覺識到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應當並可能化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而且自覺地覺識到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應當並可能化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野蠻,而入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之文明中。結果,各該當時之野蠻的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野蠻,而入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之文明中。結果,各該當時之野蠻的風夷、黃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也就先後地融化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的文明中。
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也就先後地融化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的文明中。
我們回讀歷史,讀到了這些歷史時代,讀到了這類史績,不但是不覺得我們的古先民們懷有什麼「優越感」,而且不能不驚嘆他們之自我認識的正確。自然,這一個充溢著自覺性和創造性的自我認識,不是他們於輕易中隨便得來,而是一個在豐富的歷史事實的積累中,經過了客觀的啟示和主觀的思維而始有所會心的收穫。
秦漢而降,一直到清代中葉,我們的四鄰兄弟之國,始終是稱我們這一個由「禹績」、「九有」、「中商」、「華夏」和「諸夏」脫胎而出的「中國」之「國」或「中國之國」為「天朝」、為「上國」。
這類稱號之過分的名貴或過分的尊嚴,或不無有失我們「中國之國」之平易謙沖的本色。但由此正可藉以說明「中國之國」在客觀存在中之真實的狀貌和動態之為如何。我們的四鄰兄弟之國既然是真切地看到並感到,在她們的面前有一個高貴的、莊嚴的、偉大而和平的「中國之國」的存在,也就不由得不泛露尊崇和景慕之情。自然,相對的,這一個「天朝」或「上國」也一向是很明白地理解著並重視著,她自己在東方世界之內、或諸兄弟之國之間,所居的地位和其應負的職責。
這一個「天朝」或「上國」一向是很明白地理解著並重視著她自己在東方世界之內、或諸兄弟之國之間,所居的地位和其應負的職責之具體的表現,就是這一個「天朝」或「上國」之在東方世界之內、或諸兄弟之國之間,一向是主持著正義和公道。我們若說「中國之國」在過去是如何地努力於「以大事小」,或會被他人認為是一種很迂闊、很虛偽的不經之談,然在正義和公道之消極的一面,她確是一向地以洋洋大國的風度謹守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忠恕原則。自然,她一向努力的所在,多在於正義和公道之更積極的一面。而此積極方面之莊嚴的表現,自以她「興滅國,繼絕祀」的主張和實踐最為特殊。她這種「興滅國,繼絕祀」的王道精神之所由產生,與其說是由於她四鄰兄弟之國之稱她或奉她為「天朝」或「上國」之故,無寧說是由於她自己之一向的具有「她自己乃是一個『天朝』或『上國』」的自覺和自責。例如秦之後和清之前,代表著諸不同歷史時代的「中國之國」之「漢」、「唐」、「宋」、「明」諸稱號,在原初,因只是一些王朝或朝代的名號,然因各該時代「中國之國」之政治經濟和文化之特別的繁昌,以及其對外關係之驚人的擴大,這一些王朝的或朝代的名號卻都漸次地擴大為各該歷史時代之「中國之國」的國名,或各該歷史時[代〕之「中國之國」之政治和文化的名號了。當漢人、唐人、宋人、明人,或漢、唐、宋、明之後的後人,對外提說「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如何如何,或「漢」、「唐」、「宋」、「明」如何如何的時候,他們所說的漢、唐、宋、明已不再是一個王朝或朝代,而是各該時代的「中國之國」,或各該時代之「中國之國」的政治或文化。而並且當他們說的時候,他們意識著他們所說的這一個「大漢」、「大唐」、「大宋」、「大明」之「中國之國」之於各該當時之已知的世界,就是一個「天朝」或「上國」的自稱或代詞。久而久之,這一些「漢」、「唐」、「宋」、「明」等字的使用,尤其是「漢」、「唐」二字的使用,也就於無言中含有中國政治或中國文化之在各該當時之為如何的「文明」、「進步」和「偉大」的自覺和自尊。
秦清之間,中國人之自稱「中國之國」為「漢」、「唐」、「宋」、「明」,或「大漢」、「大唐」、「大宋」、「大明」,而於謙沖敬誠之中接受「天朝」或「上國」之地位和職責,正同先秦時代,中國人之自稱「中國之國」為「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或「中國」,而於「文明」和「野蠻」的識辨之中接受了「文明」者的地位和職責一樣。這不是由於我們古先民們的狂妄或自大,而是由於他們的自覺和自責。惟其自覺,才能自責;亦惟其自責,才加強著他們的自覺。
但世變推演,今已非昔,歷史環境、或歷史發展之於中華民族,自不會永世如一。由於近百年來東西兩大世界之猝然地相遇和相交,曾給予中國歷史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局。而我們的前輩人、甚至我們自己這輩人,也就全無準備地置身於這一個非常的歷史變局之中,而為她所困惑。清末人不認識與他們猝然為鄰的新鄰人(西洋世界的民族和國家)、誤解著與他們猝然為鄰的新鄰人,雖尚知守護自己、重視自己,然實已不再認識自己,並開始誤解自己了。他們於中國幾次地被西洋戰敗之後、自己的生存已大受威脅之時,仍是堅持著中國是「天朝」、是「上國」,葡、荷、英、法、德、俄、美、義等國是「蠻貊」、是「四夷」,不但是不足以說明中國人之仍然具有自我認識,正是反面說明著我們的前輩人之不肯正視新的事實,已開始誤解著自己。他們不知道,中西相遇之後的新世界,已非我們古先民們所處的舊天地。
居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今日,屬於「歐風美雨」已經侵襲到地球上每個角落的今日,如果有人仍然是閉著眼睛,像清季同光時代(編按:1862-1908年)的士大夫一樣,極頑固地堅持道:「中國是天朝、是上國,英、美、蘇、荷、法、比、德、義、西、葡等國是蠻貊、是四夷」,自是一篇極過時之論。民初以來,講這話的人已經不多了。然民初以來,一般國人雖稍知我們的鄰人,卻忽視了我們自己,甚至否定了我們自己。因而,他們正像清末的人一樣,甚至有甚於清末的人,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是認識不清,便是犯著嚴重的誤認。
民初以來,甚至是一直到最近之最近,一般國人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的自我認識究是如何的呢?他們曾經如何地介紹我們「中國之國」呢?
講起來(若是認真的講起來),則至為遺憾。除了極少數之先知先覺者,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外,就一般的講,一般國民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總是懷著一種極模糊的概念。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外強中乾的說:「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眾的大國」,或「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也有人無所謂的說:「中國是一個老大帝國」,或「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還有人更斷章取義的說:「中國是一個弱小民族」。這是一些何等粗俗又何等膚淺的解釋,尤其是後者,更是一個何等幼稚而有害的自我介紹啊!
此外,另有一種人,固不像一般人對於我們國家的自我認識之模糊和不負責任,但不幸,他們卻又為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西洋國家──狹隘的民族國家──的觀念所蔽。這些人,大多是受過西洋近代文化的洗禮,而且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人。他們不提到「國家」二字則已,一提到「國家」二字,總是認為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如英、法、義、德、俄、美等國家,才是「國家」。因而,當他們一談到中國,或有關中國之諸問題的時候,就馬上意識著一個西洋國家,從西洋國家的「國」字的各角度來觀看中國、或來審判中國,來觀看或審判有關中國的諸問題。或者是他們先胸有成竹地拿著西洋國家的模胎、範疇或尺度,漫無彼此地向「中國之國」的臉上比、頭上坎、身上量。比來比去、坎來坎去、或量來量去的結果,很容易地會使得他們極悲觀地覺得:我們中國既不像英國、美國、法國,也不像德國、義國,也不像俄國,乃是一個四不像的國家;中國人一向是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國家觀念,真是像「一盤散沙」一般。因而,就有人會同意極少數外人之皮相的說法,認為「中國的文化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因而,也就有人認為我們「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因而,也就有不少的人覺得我們中國事事都不如人,自慚形穢地廁身於英、美、法、德、義、蘇等國家之林。直到現在,不少的國人還在嚴重地誤解著「抗戰建國」四字所涵之正確的意義。他們似乎是把戰爭當作是一個奇蹟,我們中華民族將會從這一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這自是等於說: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在無國家、無組織之非政治或無政治之生活中鬼混了幾千年,從明天起,我們中華民族要一躍而登於「國家」之域,才開始過有國家有組織之政治生活。而且這種即將開始來過的國家生活,不是德義式的國家生活,就只有是英美式的國家生活了。
誤解所及,影響極大。因為「中國之國」之不像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一方面是直至最近之最近,還在苦惱著不少的學者和專家、不少的有心人、不少的愛國救國的志士們;而另一方面,也就有不少的人由動搖到幻滅,懷疑了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前途。抗戰軍興,一部分意志薄弱之徒走向漢奸投降的死路去,大部是由於這種動搖和幻滅的意識在作祟。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之能繼續邁進、以及當此世界強國頻頻銷亡之頃,中國國家獨能於此驚濤駭浪之中年復一年地平安渡過,一般國人的自信和自尊,固已千真萬確的較之戰前大為增強。而同時,由於中國之能於此短短的數年之內,從所謂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以及無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絕地,迅速地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堅固的團結,並能另以具備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濃厚的國家觀念的新姿態和世界相見,同大敵周旋,前此痛詆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過激論者或悲觀論者,因已格於這一個新的情勢,不能不改換論調。然此等自信自尊的增強,以及悲觀論調的改換,只不過建築在一般的國人和世人對於「中國之國」之在此大時代中所有表現之極表面的反應,並非是已達到自發的理解了「中國之國」的本身的特質。
這期間,在中國的諸盟國中,不少的名流學者、甚至第一流的政治家們,曾一再地為「中國之國」在最近五年中所作之偉大驚人的表現和成就表示欣喜,然亦曾一再地為「中國之國」在最近五年中所作之偉大驚人的表現和成就深感困惑。因而,他們時時地對中國發出苦悶的或無名的讚頌。待到緊隨著中國之長期抗戰而來之最後勝利的在望,與整個亞洲之政治覺醒,迫推著國際政治轉入於一個嶄新的新時代,英美兩國已不能不於去冬採取重大步驟(編按:1942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放棄在華特權,改訂平等新約),宣告廢除各該國在華之治外法權(編按:實指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及其他有關權益,中國的國際地位已隨之而來一突進的時候,一般國人也就開始大談其「中國已是四強之一」的強國論。這不但意識著中國在戰後一定會建造成為一個像英美一樣的強國或英美式的強國,而且意識著我們中國在尚未「建國成功」之前,即已是一個「強國」了。等於說,我們中國之「建國成功」,倒反落在我們中國之已經成功為一個「強國」之後了。
不僅如此,或可說惟其如此,近五年來中國在亞洲大陸上所作之表現與成就,和由此等表現與成就即可推而知之的偉大前途,已漸次使得世界各國、甚至我們的盟邦,不無為之「一喜一懼」,終至惶惑不安了。緊隨著英美在華特權之自動廢棄的宣布,在英美兩國之內,已有不少神經過敏者、或極端自私自利的人們,出而高唱其對華早作戒備論。他們認為:「具有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如讓其民族主義自由發展,是會很容易地構成世界和平的新威脅。」因而,他們主張:「在戰後的遠東,應建立起一種平衡力量或均勢制度,使中國在亞洲不致於獨自強大、或過分強大。」結果,為平息這種錯覺的蔓延,竟勞得我們的最高領袖不能不於此對敵作戰正軍書旁午的時候,出而向世界、向盟邦,特作明確而嚴正的聲明:「中國絕無意領導亞洲」。1942年2月,蔣介石出訪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並不顧英方反對,拜訪了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10月29日,蔣在對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中澄清:他「毫無一點干涉印度內政或其他的企圖」,還進而解釋說:「我們中國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無論對印度、緬甸、越南、暹邏,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應該一視同仁,盡力扶助,不好存一點『民族優越』的心理!……我們不好蹈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覆轍,說我們中國應該作亞洲各國的領導。『領導』兩個字如果解釋得不當,就要引起許多誤會;大家以後無論說話作文,不可再用『領導亞洲』字句。……我們中國對於亞洲弱小民族,根本就只有扶助其解放的義務,而沒有要求領導他的權利,我們這一個宗旨,可以公諸世界各國,並可擔保我們將來必以事實證明。」10月31日,蔣又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閉會時講:「我們中國為亞洲最大最古之國,但我們決不要侈言什麼『領導亞洲』。」羅夢冊本人就是第三屆參政員,在現場兩度親耳聽聞,故深有所感。7
這種以人為的方法增加同盟國家間的誤解,固不無部分的事出有心,然而大部分的造因,卻不容不說是由於他們之太不了解了「中國之國」。自然這種「不了解」的責任,與其委之於我們的盟友,還不如歸之於我們的自身。我們在前邊,不是已經反覆地說過了,一般國人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不是認識不足,便是犯著嚴重的誤認嗎?自己尚且如此,還怎能反責我們的鄰人。
但所幸,當我們中華民族從近百年的歷史困頓中漸漸翻身,開始踏上復興或重獲自由之途的時候,或可說當中華民族即將為自己的歷史另開一個新時代的前夕,不無有極少數的人已潛從「妄自菲薄」與「妄自尊大」的間隙之間,轉進於「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另一境地。適於此際,在中國學術思想的領域內,歷史學、政治學以及哲學等學科的水準也達到了驚人的提高,已有可能使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在對中國國家和中國歷史之「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深處,漸次辨明近年來為一些自命開明的士大夫、或可說為一些悲觀派的憂國之士們,所倡導之「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的論調的謬誤,以及近一時為部分的英美人士所放播之「自由強大的新中國即將是世界和平的新威脅」的流言之荒唐。並進而確認:中國不但早已是一個國家、早已有一個國家,而且這一個氣派偉大、性格溫和、生活豐富而生命力最為堅韌的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和西洋近代政治產物的民族國家,以及近中東世界與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乃是三種生長並存在於不同時空之中之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政治精神和國家形態,不能混為一談。
為了尊重歷史的尊嚴,或可說在我們面對偉大祖國之光榮的過去、偉大的未來,以及其現時代的苦難和被人誤解之嚴重,來一個痛澈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後,卻使得我們不能不立即坦率而莊嚴地向國人提醒,並向世界宣告:
中國或「中國之國」,在過去、或可說一直到現在,不是一個「族國」(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帝國」,而是一個超「族國」反「帝國」的「國家」;而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而是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惟其她是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她才不是一個狹隘的排他的「族國」,也才不是一個征服鎮壓式的「帝國」。
就某一方面講,無容諱言的,「中國之國」現正落伍於西洋「民族國家」之後;而就另一方面講,「中國之國」早已走在「民族國家」和古今「帝國」之前,比之「民族國家」和古今「帝國」來得前進的多多。「抗戰建國」四字之正確的意義,是不應把戰爭當作為一個奇蹟看:我們要從這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或我們要從這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英美式的國家、或德義式的國家、或中世紀蒙古式的世界帝國來。而是應把戰爭當作是一件必要的或最後的手段看:我們中華民族現正以戰爭作為最後的手段,掃除並解放「中國之國」──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所遭受的威脅、迫害與障阻,使得「中國之國」──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能夠自主自由地生存於現世界之上,並能夠自主自由地從中古式的經濟生活中過渡到鋼、鐵、媒、電、油的現代。然後再以她的新地位、新生活,與由此新地位新生活所產生的新力量,為世界的和平、人類的福利,作巨大的貢獻。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是說中國之已為或將為英美式或德義式的強國,而是說「中國之國」之已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中國人在過去,不是不能夠把中國建造成為一個國家觀念濃厚、民族意識強烈之狹隘的或緊嚴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不能夠把中國建造成為一個由征服而統治之鎮壓剝削式的帝國,只因為順應她以前所獨處的時空的要求和歷史的發展,未走向狹隘的、排他的征服鎮壓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之路,而邁上寬大容忍之兼容並包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也就是中國人所一向稱頌的「王道精神」)之途。結果,乃「薄狹隘排他式的民族國家而不為」,亦「薄征服壓榨式的帝國而不為」,建立了並保持著一個寬大的、承納的、超「族國」、反「帝國」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
由於「中國之國」的處境的丕變,或可說由於中國歷史或東方歷史大變局之突然迫來,中華民族須要把中國之既成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加以適時的改造、或痛澈的修正與補充。須要使中國人民也起而重視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最好說,須要把這一個「中國之國」從「遺世而獨立」之「悠閒自得」或「無為而治」之政治生活中,和馬車帆船與手工生產之古舊的經濟生活中,過渡到適於國際共處之熱辣的國際生活中,和機器生產之鋼、鐵、媒、電、油的現代的經濟生活中,自是不容我們否認或忽視之鐵的事實。但為求適應上述諸需要的施政或國策之能達到正確的設計和執行,不致誤入歧途,或不致「自我誤認」或「被人誤解」,一個先決的問題卻須要首先解決。
這一個先決的問題,就是:我們須要首先理解何為「中國之國」。我們須要首先理解,正如我在前面之所宣告者,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和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與近中東世界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乃是三種生長並存在於不同時空之中的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和國家形態。遠在東方世界和西洋世界相遇之前,中國不但早已是一個國家、早已有一個國家,而且這一個「國家」,還是一個超「族國」反「帝國」的「國家」;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
客觀存在中之這一歷史事實,也就是中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這一歷史事實,也就是「中國之國」是一個超「族國」反「帝國」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這一歷史事實,乃是古今〔以〕來有關中國之一切問題的核心。
若是不具有這種認識,只是「依樣葫蘆」地站在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的觀點上看中國,或以近中東世界和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例中國,則我們自必為嚴重的錯覺所誤。有鑑於過去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缺乏,以及中國人民之確如「一盤散沙」,不但是會同意少數西洋人所倡之「中國文化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的謬說,而且是不能不認定中國人的政治才具是低能、是劣等。人家早已各自建立起一個民族意識濃厚、國家觀念強烈的民族國家,我們遲至今日還未能。再不然,剛剛相反的,看到今日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的勃發、國家觀念的強烈,也就會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突變,轉而認定,所謂「建國」,就是中國要很快的建造成為一個英美式的「民族國家」或德義式的「民族國家」。甚至,中國民族主義之過分發展,即將會變成為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全能國家,再來一次中世紀之蒙古式的外侵,坐使全世界為可怖的「黃禍」所氾濫。在這種嚴重的錯誤認識下,我們不但是再讀也讀不通中國史,而且是再談也談不通有關中國之一切問題了。要談的話,是一談就錯。但反之,如果我們打破了西洋近代「民族國家」之國家觀念所加於我們的桎梏,並排除近中東和歐洲之古今「帝國」所給予我們的暗影,理解了上述之重大的基本要點,則我們不但是能夠左右逢源地讀通了中國史,一談到有關中國的問題的時候,就會馬上抓著它的重心,而且是將會恍然地覺悟到:惟有中國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文化;也惟有中國文化,才是人類社會中最和平的政治文化。中國人的政治天才、組織能力,以及其爭取和平和維持和平的魄力和決心,不但是高躋於世界上和歷史上最富政治才能之古代的羅馬民族和近代之盎格羅薩克遜民族之林,並超而過之。
講到這裡,或須要我們及時地鄭重指出,我們所作之上述論述,乃係來自於客觀存在中的歷史史實,非出於著者之閉門杜撰。讓我們就在接下的篇幅中來一個簡要的說明。(待續)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