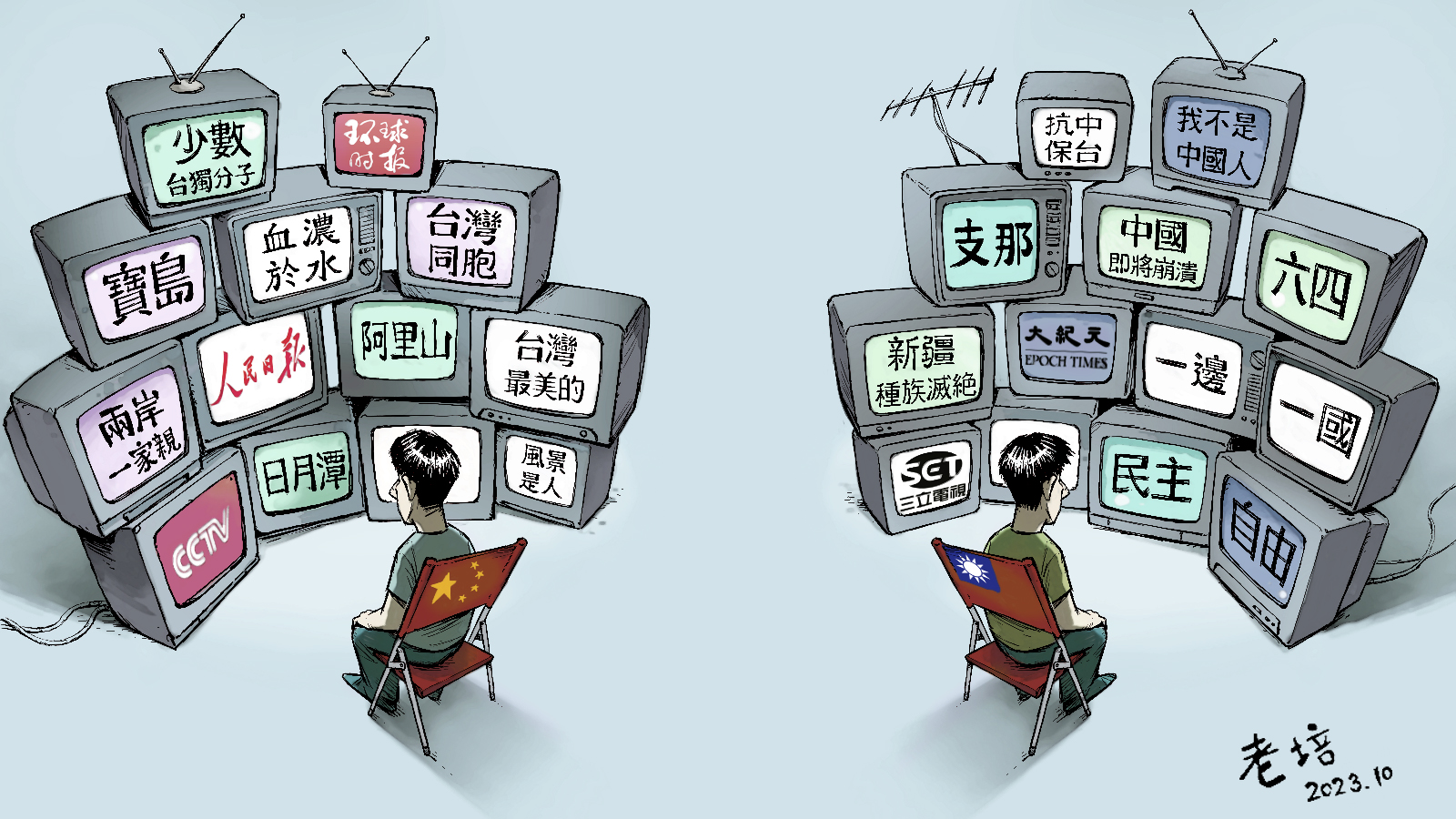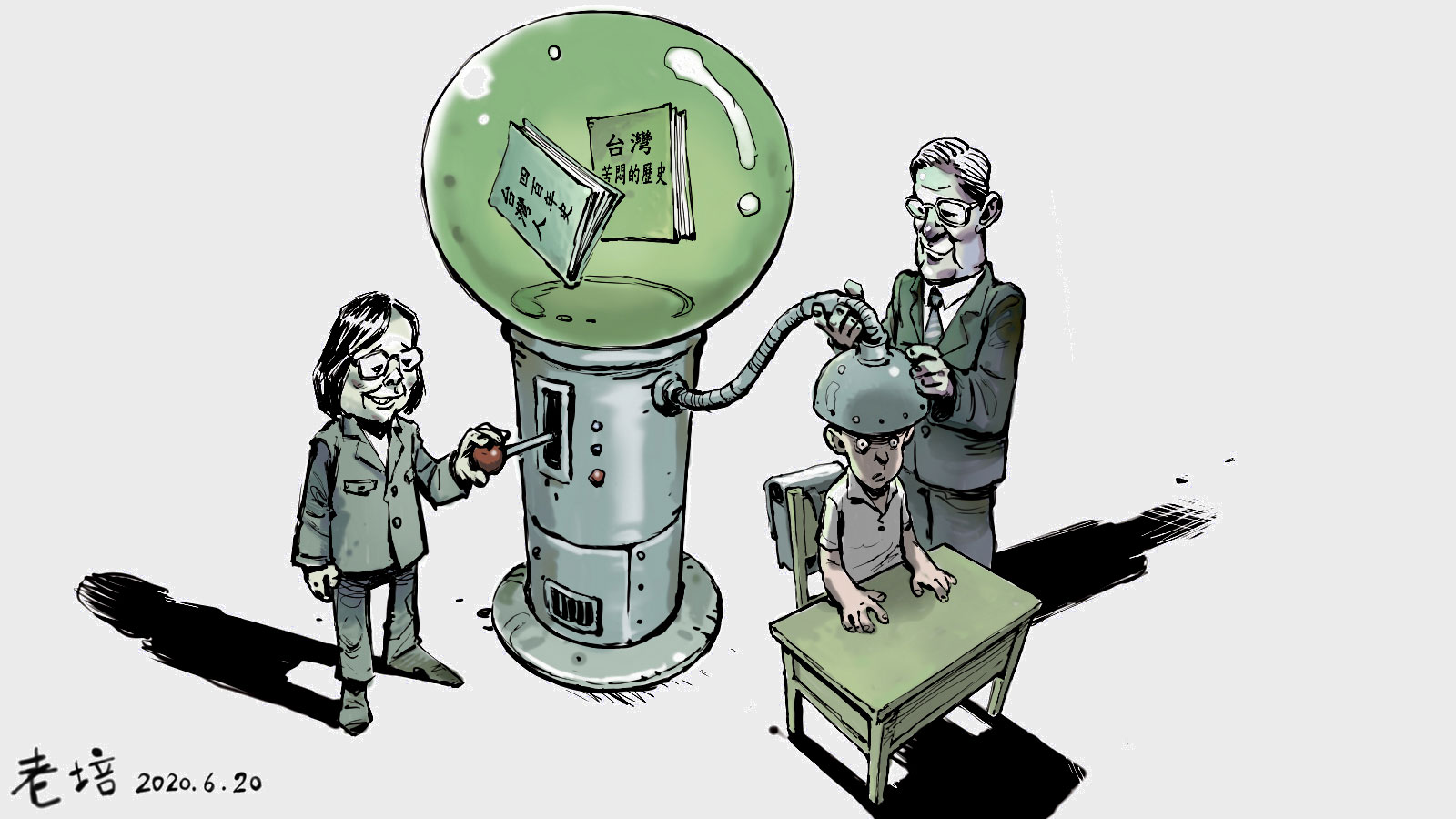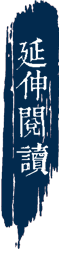近來,語言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一些人在談論「語言權利」和「認同政治」,對於「國家通用語言」政策產生了一些疑問。
從歷史的角度看,單一的「國家語言」制度在西歐民族國家強力推行,在西歐的體系下,語言成為公民身分認同中主要的構成部分,也成為「國族文化」的主要成分之一。
西歐民族國家體系下的一元語言政策
語言是人類的溝通工具,人類在地表分布的廣泛性,導致了語言的多樣性。語言多樣性本來是文化現象,但這個現象很快就與政治連結,成為「前民族」(pre-nation)的一種標誌。然而,從「前民族」現象演變到「民族國家」有一段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言邊界與政治邊界通常並不重疊。事實上,在歷史和當代的現實生活中,不同語言之間的接觸和由之產生的多語現象一直是生活的常態,當今世界的大多數人都能說一種以上的語言或方言;在民族國家的概念興起之前,單語現象通常只存在於小型島嶼,連不列顛島這種規模的島嶼,直到15世紀都還有5種語言並存,英語僅是其中的一種。
中世紀晚期,在西歐部分地區,語言開始上升成為身分的依據,繼而又成為衝突的根源。西歐各國的君主和他們的大臣開始把統一的語言,至少是統一的行政語言,看作是對國家的支持,還可以鼓勵對國家的忠誠。17世紀後期,步入民族國家化道路的西歐和北歐諸國,出於政治整合──而非文化整合──的目的,開始在學校推行單一語言教學,禁止在學校甚至日常生活中使用那些不是由君主使用的語言。儘管在這時,語言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定義下的nation(後來被中文譯作「民族」、「國族」)還沒有建立固定的連結,但單一語言政策加速了西歐中世紀國家轉型為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進程。從18世紀中期開始,語言與民族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西歐國家事實上奠定了「一個國王、一種信仰、一部法律、一種語言」的觀念;而語言,尤其是口頭語言,成為聚集「民族」(nation)最有效的工具。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已經訴諸以「語言革命」為重要內容的政治革命,試圖建立法語在法國境內的唯一合法地位,而革命的目標果然達成了,巴黎以外的學童,在教室乃至操場上不說法語,就會受到懲罰。
「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普及,使得「一個國家、一種語言」的觀念被西歐視為理所當然,並幾乎同步蔓延到被歐洲殖民的美洲大陸。新興的美國,理所當然地排除了當地印第安人的語言,也排除了西班牙語等其他歐洲語言,將英語定為「法定的」和國民教育中應用的唯一語言;中南美洲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新國家,也規定印第安人必須學習殖民者的語言。1789年之後,在西歐和北美國家,國家軍隊、全民教育和公共媒體體系的不斷強化,造就了「印刷資本主義」下的民族國家單一語言的絕對優勢。在此基礎上,官方進一步規定語言標準,透過制定語言政策鼓勵或壓抑公民對特定語言的使用。學校、文學作品、交通和傳播設施的進步,則進一步有效推動了民族國家單一標準語言壟斷的進程,國族形塑的程度得到進一步加强。今天,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尊重少數族群文化權益、保護多元文化的壓力下,整個西歐、北歐和由西歐移民建立的美洲、大洋洲新國家在生活層面接受語言多樣性的現實,但在國民教育中依舊堅持一元的語言政策。
西歐民族國家體系以外的語言多樣化常態
在西歐民族國家體系之外,長期以來,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體系並沒有將語言多樣性視為對政治的威脅,歐亞大陸大部分區域的傳統國家對多語現象都抱持寬容的態度。直到19世紀,「一個國家、一種語言」的觀念才蔓延到中歐和東歐,到了20世紀,「單語制」或單一的「國家語言」制度始成為「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中普遍接受的制度。即使如此,包括現代中國在內的許多非歐美國家,在國家語言政策及實踐,包括國民教育中,依然沒有實行「單語制」。
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中歐、東歐在政治上尚未進入西歐「民族國家」體系,對宗教的尊崇和對多語的寬容是兩個並存的現象。但在西歐政治的影響下,中歐、東歐不同語言的使用者,開始將取得語言的自主性與取得政治的自主權連結在一起,這個時期追求「語言純潔性」的運動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20世紀初期之後,中歐和東歐在政治上紛紛效法西歐民族國家,在語言上也展開淨化運動,取消了對多語的寬容。
整體而言,西歐版本的「單語制」隱含著針對少數族群語言的壓制,它成為西歐版本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側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則開始針對歐美民族國家「單語制」的政治文化現象作出反思和反制。列寧將推行俄羅斯文化壟斷政策的沙皇俄國稱作「各族人民的監獄」,宣示在文化上尊重多語現象,倡導語言平等。列寧於1914年針對性地指出,法定語言並無必要,據此,蘇聯在1990年之前都沒有規定法定語言。1918年,蘇維埃政府宣布所有國民均可以用母語接受教育;蘇聯還透過政治和行政措施,保障全蘇境內包括母語受教權在內的多語權利。在1924年頒布的第一部蘇聯憲法中,俄語、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格魯吉亞語、亞美尼亞語和「突厥—韃靼語」(現在的亞塞拜然語)6種語言被確定為通用語言,伴隨各加盟共和國的陸續加入,這個通用語言目錄也變得越來越長。與多語制、母語受教權並行的,是政治上的「民族識別」和蘇維埃聯邦制下的民族自治制度。然而,伴隨這一制度的成形,蘇聯境內各族群間的差別較沙皇時期更加擴大,並呈現固定化的趨勢,布爾什維克黨追求建構「蘇聯人民」認同的理想遭到阻礙,這一情勢,迫使史達林於1930年代中後期,先是曾試圖創立並推廣一種「融合語言」,即包括英語、法語、俄語甚至世界語的混合語言,遭遇挫折後,又於1930年代後期將俄語定位為國家通用語言並展開推廣。但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缺乏法律定位的俄語並沒有充分展現溝通蘇聯境內各族群的功用,這一現象成為日後蘇聯解體的潛在因素之一。
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對多語現象抱持高度的寬容。近代之前,東亞各政治體、各文化群體一方面一致推崇「華夏」文化,另一方面也都以自身的方式改造「華夏」文化,其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對漢語書寫系統的利用。東亞各傳統國家和族群的母語,包括語言學上的漢藏、阿爾泰、印歐、南島、南亞五大語系的眾多語言和若干語系不明的獨立語言,即使在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內部也存在數量可觀的方言、次方言,在口語溝通上,存在某些難以逾越的障礙。但除了使用漢語的人之外,上述很多政權和族群也紛紛借用漢語的書面形式「漢字」作為本族母語的書寫工具。主要由「指事」、「會意」的原理創制的漢字,是一種視覺化的符號系統,使用不同漢語方言的人以及非漢語使用者都得以擺脫自身母語與漢語(中心方言)語音、語法不同的障礙,使用這套相對成熟的表意符號,從事複雜政治活動所需的記錄、溝通和傳播。這樣,既達成了在區域內大範圍溝通的目標,又保留了語言多樣性,這一模式的原理,成為現代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生態效仿的原型。
當然,在漢字圈的周邊,仍有諸多保留包括其特有語言文字在內的自身文化傳統的族群,其中幾個族群(犖犖大者如蒙古、藏、維吾爾)曾對於中國史、區域史乃至世界史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它們也以自身的方式廣泛介入漢地的政治和文化。如由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在文化上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形成即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出現這一結果的前提,是蒙古、色目人廣泛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元攻滅南宋後,理學、學術北進,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漢人「循利南趨」,任職、旅寓江南的色目人習儒者眾。蒙古、色目人「華」化成為傑出詩人、詞人、畫家者,數以百計,且使用漢化姓名,並非在明代才受明朝的壓迫而被迫改名。色目人在漢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極普遍,而非鮮見的現象。由於漢語、漢文並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語,蒙古人、色目人接觸和學習漢語文,反倒是從與漢人基層社會的接觸開始,以「自然學習法」,從民間口語直覺、直接地習得。元朝的官方文書,其漢文版往往使用口語體,即「白話」。元代白話文體繪本(全相本)經、史、俗文學著作開創近代文化白話文學傳統。元代的白話文也會夾雜蒙古語語法,這一現象其實呈現出遼代以來北方漢語口語的現實狀況。這樣的現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來的「言文一致」,較之秦始皇時代的文字統一,更進一步推動了國家共同語的形成。從歐洲的標準來看,國家共同語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一。

左圖為元代畫家高克恭(1248-1310)所繪製的《雲橫秀嶺》之局部圖。高克恭為色目人,自幼學習儒家經典,奠基儒學基礎。又結識許多書畫名家、飽覽江淮山水後,拾筆作畫,時人稱其與趙孟頫(漢人)南北並列,故有「南趙北高」之名。右圖攝於山東曲阜十三碑亭之一隅,亭中佇立著五十餘座自唐代至清代以來的巨碑。碑石上刻著皇帝對孔子的追諡加封、祭孔和整修廟宇的紀錄等,其中,碑面上鐫刻的文字除了漢文外,還使用了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和滿文。由此二例可見中華文化從古至今便是包容、加入式的文化集體,真正呈現多元且包容的樣貌。
現代中國文化,從衣、食、住、行開始,到語言文字,再到某些深層文化,都與日本、朝鮮/韓國等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有所歧異。日、韓等國文化當中保留了較多的「中國」中古以前的習俗、語文當中保留較多中古以前的漢語文詞彙及用法。而近古和到現代漢語,則因密切的語言接觸,吸收了相當數量的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及滿語詞彙。當然,各個歷史時期,尤其是元以後的中國範圍內,各非漢語言也吸收了很大數量的漢語詞彙和語法影響。元以後中國的服飾、餐飲習俗、建築、家庭、宗族制度,都與漢字文化圈內其他國家有了比較明顯的分別,現代中國所繼承的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化遺產,正是來自各族群文化間廣泛交流、共同參與後所留下的「中國文化」,而所謂「純」的漢文化,僅僅存在於漢人和少數族群中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想像之中。
從「單一」到「通用」──20世紀中國語言政策的轉折
13世紀到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歷史依照自身的內在線索和邏輯,逐漸走上由「天下國家」轉型成為「領土國家」的軌道。然而,西方殖民者的到來,迫使中國中斷這一轉型進程,被迫效仿西歐民族國家模式,轉到中華民族形塑和民族國家建構的軌道。如上文所述,西歐民族國家將推行單一的「國家語言」視作國族建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19世紀,在民族國家建構進程中起步比較晚的德國,也開始推廣由國家頒布標準字音、語音、語法的語文改革運動「國語運動」。20世紀初,清朝開始效仿西歐民族國家,啟動中國的國語運動,1909年,資政院議員江謙主張將漢語官話改稱為「國語」;中華民國成立後,繼續推行國語運動,由國家推動的「國語教育」規模逐漸擴大;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等人又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對「國語運動」也產生正面的推動。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明確國音應當以實際存在的口語語音作為標準,並一致通過將北京語音為國語標準音。
受到布爾什維克民族平等觀念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期間,意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廣袤多元的國度裡,執政者對於「國語」的定位和推廣,可能帶來壓制少數族群文化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政治上採行「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在文化上相應實行扶持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政策。為尊重少數族群使用的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此前中華民國政府所稱的「國語」改稱為「漢語普通話」。
「漢語普通話」的定位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漢語與其他非漢語語言在地位上平等;其二,「漢語普通話」是使用各非漢語語言及各漢語方言人們的共同交際語。換言之,「國語」與「漢語普通話」的差異在於,「國語」是單一的「國家語言」,而「漢語普通話」是國家的通用語言,它著重「通用」,而非「單一」。
從政治的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延續了清末和中華民國的國族建構方向,但它在中華民族建構的方法和內容裡,加上了中國的多元傳統與布爾什維克民族平等的精神,修正了西歐民族國家的模式,使之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及中國境內各族群的文化利益。因應國族建構,維護和促進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的需求,國家有必要推廣通用語言,國家內部的非通用語言使用者(不論其為少數族群或漢人)也有學習通用語言以滿足人際交流與個人發展動機的需要。因應保護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國家也有必要保護國家通用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和方言。(關於「中國民族識別政策」,參見《遠望》2018年3月起連載的吳啟訥〈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
蘇聯和中國開啟以保護文化多樣性為內容的「另類」國族建構方向之後,學界也逐漸體認到文化差異性與語言多樣性保存的意義。研究者發現,語言滅絕在人類歷史上一再發生,20世紀以來的新殖民主義和全球化加劇了這一趨勢,經濟上強大的語言凌駕在其他語言之上,使用人數較少的語言瀕臨危機;研究者看到:有許多因素影響著人類語言的存續和使用,其中包括母語使用者人數、地理分歧程度與該語言的使用者在世界上的社會經濟影響力等;他們認為,國家可以透過語言政策強化或消弭這些因素。在蘇聯、中國和學界的影響之下,20世紀後半期的西歐、北美國家才有條件、有限度地實施文化多樣性和瀕危語言保護政策。一些國家開始藉助語言政策來保護地區性語言或瀕危語言,儘管他們依舊認定少數族群語言的存在可能成為國家內部融合的潛在障礙,但也同時體會到保障公民的語言權利有助於提升公民對中央政府信任度的政治效應。所謂「有條件、有限度」,主要指的是這些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當中,單一的國家語言依舊是唯一的學科知識教育語言。與此同時,仍有很多國家堅持單一民族和單一國家語言政策,如日本依舊傾向漠視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編按:即愛奴人)與琉球群島原住民的民族身分和語言權利。
保護多樣、鼓勵通用的當代中國語言政策
保護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保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是蘇聯和當代中國在政治設計與政治實踐中推行的政策。這一政策對源自西歐國家的「單一國家語言」政策做了大幅修訂,對學界和公眾的認知產生了影響,但直到20世紀的最後一段時間,這一政策的方向才成為知識界的共識。
當今世界上有約兩百個國家或政治體,卻依舊存在大約六千種語言。這說明:大多數國家內部還是存在多種語言,因而大多數語言仍然會與其他語言密切接觸,單一「國家語言」制度仍然需要藉助「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理想設計和與之配套的政治、行政、教育措施才有實施的可能。「前民族國家」世界、蘇聯和當代中國都是在尊重語言多樣化現象的基礎上制訂和推行語言政策的。西歐、北美國家「單語制」實踐的缺失,凸顯出西歐民族國家模式下的文化政策的盲點。

圖為中國和美國的紙鈔,中國的鈔票上使用了蒙文、漢語、維吾爾文、藏文以及壯文,反觀,聲稱「多元」、「包容」的美國,美鈔上卻只使用了英文。
然而,在「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主導當今世界的現實中,想要回到「前民族國家」時代,已不可能。人們也必須面對語言會隨時間演化、分化乃至消失的歷史規律,面對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單位劃分並發展國族利益的現實,在國族建構和保護少數族群文化、保護語言文化遺產的目標上尋找平衡點。觀察1990年代以來中國各族群的語言生活,可以看到兩種現象:其一,伴隨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和國家整合程度的提升,非漢語族群和漢語方言區民眾對於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的需求大幅上升;其二,伴隨非漢語族群和漢語方言區民眾生活水準及教育程度的提升,民眾對於保存、學習母語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有所提升。當代中國保護「多樣」、鼓勵「通用」的語言政策,正是建立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