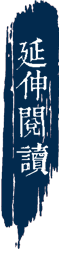國軍開到台灣以後
(一)又開始了被困的生涯
〔3月9日〕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了。但臺北城中的槍聲,仍像昨夜一樣的密集,不過聲音好像已經稍為遠了一點。我們連忙爬起來洗了臉,吃了點東西,想到外面去探探風聲。然而一陣陣的噓噓的槍彈聲,依然像流星一樣的劃過天空;有的,甚且更掠過植物園中的林梢,卜碌碌的掉下來。在槍彈橫飛中,我們怎麼能出去呢?又到什麼地方才能探聽消息?沒法,我們只好開開收音機,想收聽一點廣播,希望從無線電中,能夠收聽到一鱗半爪的消息。於是,我們便全部都圍坐在收音機旁傾聽。但聽了半天,收音機好像啞巴一樣,一直沒有聲響。自從臺北二二七事變發生,民眾控制了臺灣廣播電臺以後,差不多每日自晨7時起至深夜12時半止,幾鎮日哇啦哇啦的廣播不停。我們起先還以為機件發生故障,後來一檢查,方知一點也沒有什麼毛病。
3月9日自晨至午,我們差不多在收音機旁坐了五個多鐘頭,一直等到下午1時許,我們才從收音機中,聽到了二二八處委會廣播撤銷「四十二條」的聲明。但自此以後,我們便沒有再聽到過該會廣播的消息。在這時,我們心中雖然仍是忐忑不安,但已沒有昨夜恐懼的情緒,我們猜想:也許國軍已經來了吧?要不然,臺灣廣播電臺哪會如此沉默?在那時,我們是多麼熱切的,渴望著國軍能早日開到臺灣啊!因為臺灣的兵力太空虛,因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不能保障外省人的安全,致使很多外省人都喪失了生命,更使很多外省人因此而痛恨陳儀、詛咒陳儀啊!
自從〔3月7日〕處委會向陳儀提出了「四十二條」以後,我知道有些要員們已備好飛機,預備於必要時可以隨時撤離臺灣。而海關招商局,與臺航公司的職員,復控制了大批的船集,也準備到緊急時,可以隨時乘輪離臺;是以臺灣航業公司在事變時,特別由臺北遷到基隆去辦公,其目的亦即在此。至基隆、高雄兩地海關中,有些高級的職員甚且已有一部分自臺灣撤至福州去辦公。當那些可憐的外省籍的小公務人員們看到了這種情形、聽到了這種消息時,他們真是悲傷極了,也憤恨了。我在臺南、臺北時,有很多外省人都曾向我哭訴著說:「要人們太太的洋狗洋貓,都有機關槍衛隊保護;我們這些小公務人員們的生命,便無人聞問。難道我們的命便真的趕不上她們的洋狗洋貓嗎?」像這種不平之聲,幾到處可聞。而陳儀之弟陳公銓,與葛敬恩夫婦之公館內,自從被忠義服務隊檢查並投炸彈後,即搬入長官公署內去住宿,以避災難。但那些小公務人員,便只有在恐怖中過著飢餓的日子……。
〔3月9日〕風停雨止,植物園中寂無行人,淒涼如荒原;要不是槍聲頻傳,幾真像一座死去了的林園。我們困居小屋,只以閱書談笑自遣,然落寞難消,只好悵望雲天,默默地遐想。
迄至下午5時許,當我們正在沉思默想,苦心焦慮的時候,忽然又聽到收音機中清晰的廣播,謂:「基隆於8日下午2時,曾有青年暴徒百餘名,〔企〕圖攻擊基隆要塞司令部,當〔即〕與守軍發生激戰;暴徒被擊斃兩名,基隆旋即戒嚴。至臺北市區之暴徒,亦於8日晚10時半分組發動攻勢,與由北投、士林、松山等郊外之暴徒匯合後,即開始向圓山海軍辦事處臺北分處襲擊;其他暴徒,則分別攻擊臺灣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醫院,及長官公署、臺灣銀行等機關,即與守軍發生激戰。又閩臺監察使楊亮功氏,已於8日午自福州乘海平輪抵基隆港,因暴徒盤踞港口,當〔即〕與楊監察使同輪抵臺之兩營憲兵及基隆要塞司令部之守軍衝突;激戰6、7小時,始將暴徒擊退。楊亮功至下午4時始能登岸。深夜即9日晨2時,楊氏偕其隨員劉啟堃等遂乘載運憲兵之卡車,由基隆出發;沿途均有戒備。不料行至七堵與八堵之間,即遭夾道兩山間之暴徒襲擊,當〔即〕有憲兵一人受傷,劉啟堃亦被擊斷三指;楊氏幸先移動坐位,未遭意外,然已跌於車旁,飽受虛驚矣。幸賴憲兵保護,且戰且走,直至晨間3時許始安抵臺北。現本市已自9日晨6時起,宣布戒嚴。軍憲出動布崗,禁止暴徒通行……」云云。
當我們聽到這種廣播時,我們方知道昨夜槍聲的緣由,並獲悉已有兩營憲兵開抵臺灣的消息。同時,我們相信還有很多的國軍,將源源的增援臺灣,來救護我們出險!這時,我們雖然仍被困在小屋內,然心情已迥非昨夜之心情矣。
惟在廣播中所聽到的消息,只是一些官方的報道。事後,據一個權威的人士,告訴我一段幕後的消息稱:臺省當局在事變發生時,起先以為地方事件,頂多幾天便可解決,故未將詳情陳報中央。迨至3日全省各地之民眾均紛紛暴動後,始知有異,乃急電蔣主席暨國防部速派援兵。參謀總長陳誠於接獲密電後,即迅令駐在崐山之廿一師原手抄本此處寫的是「二十師」,後面為「廿一師」。此處有誤。1 劉雨卿部速調臺灣增援。同時,臺灣憲兵團團長張幕陶亦急電原駐福建之兩營憲兵迅速開往臺灣,加強實力。劉部於5日接得命令後,即星夜將廿一師部隊由崐山以急行軍開到上海,於3月6、7、8三日分乘太康等軍艦先後離滬。本擬在8日晨即可開抵臺灣,但終因船隻缺乏,較預定時間約遲一日;幸由福建開到臺灣增援之兩營憲兵,能及時趕到。否則,長官公署及其他各重要機關,均不免要慘遭「接管」之命運。
故那時云閩臺監察使即將抵臺之消息,實係一種暗號,表示國軍即將可以開援臺灣之謂。二二八處委會某些顯要們,亦明知中央遲早終將派兵來臺鎮壓,惜已陷入泥坑,無法自拔矣。
陳儀自獲知國軍即將抵臺之消息後,態度即轉趨強硬。當黃朝琴於8日晤陳儀時,曾談到政治腐敗、澄清貪污等問題,陳當〔即〕將桌子一拍,勃然大怒道:「什麼腐敗不腐敗、貪污不貪污!你有什麼證據?」說著,即逕自跑進辦公室中辦公,黃朝琴遂亦愀然而別。
自從二二八處委會向陳儀提出「四十二條」後,陳更震怒異常。遂於7日晚即暗令臺北市所有的軍隊,秘密集中待命;8日,當長官公署獲知處委會因「四十二條」問題而發生分裂時,負責軍事方面者,即於8日晚以軍警便衣密布中山堂附近,伺機而動。同時,二二八處委會激烈派的分子如王添灯等,因所提之「四十二條」未能如願,亦擬提前於3月10日接管長官公署。
長官公署於8日晚間10時許接獲憲兵已抵基隆之情報後,即於10時30分下令總攻。是時,二二八處委會的要員們,均大多分聚中山堂與日新町國民小學兩處開會,於聞及槍聲時,尚以為係民眾攻擊長官公署;及至軍隊衝進房屋時,始知有變,乃狼奔豕突,紛紛逃竄。而有武裝之流氓浪人以及退伍之軍人等,遂與軍隊展開激戰。故一時槍彈聲大作,全臺北便又陷入最恐怖之混亂中。
二二八處委會與忠義服務隊、臺灣自治青年同盟等各首腦,被捕獲者甚眾。據聞,王添灯是時正預備赴廣播電臺,走到半路上即被伏軍擊斃;其他如呂伯雄、陳金水以及處委會的顯要們,亦大半先後被捕。當軍隊跑至蔣渭川家中搜捕時,蔣是晚適不在家,蔣之兒子則被打死。蔣渭川聞悉後,乃留書一封致陳儀,大意云:「余之子不幸被打死,余已痛不欲生。從此以後,余蔣渭川將與你陳儀誓不兩立,不是有我無你,便是有你無我。」一氣而遠遁深山,發誓將領導民眾,抵抗到底。
3月9日晚,我們又聽到收音機中用國語廣播稱:「暴徒400餘人,於今日11時,圍攻水道町臺北市區偏南,約從水源路到羅斯福路三四段、溫州街、龍泉街的帶狀,今日臺北自來水源區、臺電總管理處一帶。2 電臺,與國軍駐守該臺之士兵一排發生戰鬥,情勢曾一度危急,經增援後於午後4時,始將暴徒擊退;計擊斃3名,俘獲13名。又今日下午6時,暴徒百名,曾襲擊圓山附近之輜汽二十一團;被守軍擒獲20餘名。同時,復盛傳暴徒將破壞臺北市自來水總設備,擬絕水源,並唆使高山族人民自新店方面進襲市區,本市已有戒備」云云。這一晚,我們雖然仍提心吊膽,然已呼呼的睡了一大覺。
(二)收音機中的天下
前幾天在收音機中,盡是聽到閩南話、客家語、日語等的廣播,很少用國語,幾全是二二八事件處委會的各種報告,裡面充滿了血腥的氣味,自然令我們不高興。但自從9日下午1時起,即不再聽到該會的聲音;一如事變前一樣,除了各種的唱片和新聞外,又大半是長官公署的廣播了,而在各種廣播中,也同樣充滿了血腥的氣味,自然也令臺灣人不舒服。
在國內(編按:指大陸地區),是新聞紙比廣播重要;但在臺灣,則是廣播比新聞紙更重要。因為,臺灣的收音機,據我私人的統計,至少有六萬具以上。平均每一百個臺灣人便有一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各種的消息。故事變爆發以後,民眾即首先占領廣播電臺;國軍開到以後,自然也首先收回廣播電臺。是以,從收音機中廣播的語調,我們便可以測知一件事態的盛衰。
昨夜及今晨(編按:指9日夜及10日晨),臺北市的槍聲,依然到處砰砰磅磅的響,惟已不像8日夜與9日晨那樣的密集,而只是斷斷續續的零星的槍聲。從早上7時起,我們便看到警察訓練所裡的警察,從隔壁跑到植物園中來看地形、挖戰壕、做陣地,他們在林中指手劃腳的跑來跑去,臉上顯得很神氣、很高興似的,已不像前幾天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更不時的向著遠遠的地方射擊。我們悶坐在屋子裡,想到林子裡面去逛逛,但他們卻以手示意,勸令我們不要出來,免得受流彈的襲擊。故我們只好一天到晚的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廣播,或躺在榻榻米上看小說。
3月10日上午10時,陳儀向全省同胞廣播,正式宣布國軍已移駐臺灣,與再度戒嚴的意義,並聲稱已將二二八處委會解散,其他各非法團體,均予以封閉。同時,復籲請全臺同胞:工廠須復工,商店須開門,學校須開課,不准抬高物價,不准集會遊行,不准藉口規避等。
但事實上,因為秩序未能及時恢復,物價波動更烈,米荒尤其嚴重,甚至於花60餘元臺幣的高價尚買不到一斤米,就是山芋雜糧等,也猛漲不已,有錢無市。我們在被困期間,便曾吃山芋、吃紅豆、吃糯米,吃得肚脹胃疼;而有很多貧苦的小公務員,和做小生意的臺灣人,只能日食山芋和開水充飢。
再加以戒嚴令沒有解除,有些好的臺籍學生,自從聽到陳長官之廣播後,便紛紛到學校去上課,因而被戒嚴之士兵誤擊身死者甚多。尚有很多送牛奶的、賣報的、送電信的、販賣蔬菜的、拉黃包車的臺灣人,因為不懂戒嚴令的規定,因為彼此語言的不通,致被哨兵誤擊而死傷者亦甚眾。而有少數心存報復的軍警,更以射擊人命為兒戲,有時將本來是很善良的臺灣人,也當成「暴徒」來處決,任意予以擊斃。我在某一個樹林子裡面,便曾親眼看到有些穿黑衣服的警察互以手勢作暗語,表示比賽打死人的多寡。但大多數的外省人,自從國軍開到以後,很少有對臺灣人採取報復的行動。
10日下午,在植物園中,我便聽到一個曾經被打的外省人說:「我雖然被打三次,幾乎被打死,但我不想報復,我原諒那些臺灣人的幼稚和盲動。假使冤冤相報,仇恨越積越深,從此便永無寧日,那絕不是一個好現象。」像這種悲天憫人的胸懷,我想,即使是一個殘暴不仁的臺灣人聽了,也一定會深受感動的。這雖然是一個被打的外省人之態度,但確能代表大多數外省人的情懷。
從3月9日至11日,在這三天內,我們均被困在小屋中。11日那天,據說,市區內的「暴徒」已被肅清,而槍聲亦漸稀微,我們才敢在植物園中的最裡面散散步,但仍不敢跑到林子外面去。在被困期間,除了收聽無線電外,便得不到任何的消息。故在那幾天收音機中的天下,不是某某處長廣播,便是某某局長訓話,一天到晚也是哇呢哇啦的叫個不停,老調常彈,也委實有點令人心煩。且收音機只能收到臺灣的消息,若收聽京滬一帶的廣播便比較困難。故直至11日下午5時許,我們在飛機散發的傳單中,才獲知蔣主席對於臺灣事變的態度。當我們看到那架飛機翱翔天空散發傳單時的雄姿,當我們獲知蔣主席對於處理事變那種寬大的態度時,我們的心中是多麼高興啊!
(三)臺北城中街頭巡禮
在小屋中被困了三天,一直到3月12日早上,聽聽臺北市區裡面已經沒有什麼槍聲了。於是,我們便冒險跑出植物園,到劫後的臺北街頭巡禮。因為,在戒嚴令中規定:凡民眾通過步哨線時,不准三個人以上在一起走路,並應慢步行進,不得東張西望。所以,當我們走到街上時,我們幾個人,便分成幾個小組,以不規則的三角形,一先一後的走著。更隨時提防著怕有流彈的襲擊,因為,有些狡黠的流氓浪人,還常常隱藏在偏僻的地方,或潛伏在三四層高的頂樓中,向軍隊或外省人襲擊。
一走出植物園,便是博愛路。我們剛踏上馬路沒有幾步,就看到有三具僵硬的屍體:一具躺在陰溝裡,像是一個送報的小孩,他旁邊還掛了一個褪了色的報袋;一具橫臥在大馬路上,殷紅的血濺滿了一地,因為身體是伏在地上,看不清面部;另一具則是一個送牛奶的青年,很多破碎的牛奶瓶子,還零亂地散布在死者的身邊。當我們走到前日本總督府的附近時,又看見了幾具屍體,橫七豎八的躺在大馬路上,屍旁地上,血跡斑斑,附近爬滿了蒼蠅,發出一陣陣的惡臭,令人作嘔。而有些地方,雖然屍體已被移去,但死者破爛的衣服,依然殘存在地上。沒有主子的野狗,更常常啣了一隻人腿或一個骼髏,在荒僻的防空壕旁啃噬;有些野狗更啣著死者的皮靴、鴨嘴帽、內衣等,在馬路上到處奔跑。而在每一條馬路上,幾乎到處可以看到一攤攤的血跡。這正猶如在二二七事變發生以後,臺灣人毆打「阿山」時是一樣的情況。
今天是總理誕辰原文如此,應是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紀念日之誤。孫中山生於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過世。3 ,故臺北城中,均到處掛滿了國旗,無論大街小巷,均崗位森嚴,哨兵林立,每一支槍桿上,皆插著雪亮亮的刺刀,槍膛中並上好了子彈,每一個雄赳赳的憲兵,和一個氣昂昂的軍隊,都精神抖抖的注意著每一個行人。8日以前,在馬路上是看不到外省人的,但今天卻恰恰相反,很少有臺灣人在街上走動。偶而在街上走著或騎在腳踏車上的臺灣人,臂上也都纏著警備總司令部所發的特別通行證;從他們那種惶惑的形色中,我們可以猜測他們心中的疑懼。今天,我看到很多外省人和公務人員,都敢抬著頭在街上走路了。前幾天,他們是連看都不敢看臺灣人一下的。
最令我奇怪的,便是大多數臺灣的女人,他們自從國軍到了以後,均不敢穿著木屐再在街上徜徉,十有八九,都已換上了皮鞋。故木屐聲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的刺人耳朵。說句老實話,我對於臺灣同胞所穿的那種日本式的木屐,實在有點憎厭;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只要一聽到那一陣陣滑泥滑踏的聲音,我便感到難受。也許那是因為過去痛恨日本人的關係罷?
我從博愛路一直走,便到了火車站。又從火車站向右拐,轉向太平町;未穿過鐵道,我即被哨兵擋駕。據說太平町一帶仍藏有「暴徒」,正在繼續搜捕。沒法,我便只好從臺北電信局營業處的門口折回來,又向長官公署那邊走去;但走到中山路與中正東路圓環附近時,又被哨兵擋駕。於是,我乃在衡陽街、懷寧街、沅陵街一帶漫步。只見在這一帶街道上的商店已大半開門,做生意的臺灣人,對於每一個外省人去買東西,都戰戰兢兢的特別客氣,一反以前那種傲慢的態度。對於國軍去時,更常常自動減價廉售,以博取國軍的歡心。各機關有的已局部辦公,但未開始辦公的仍占大多數。劫後的臺北街上,一切都顯得淒涼冷落。
後來,我更特別跑到中山堂去憑弔了一下。只見四周哨崗密布,裡面則靜悄悄的闃無一人,與我8日那天下午來看時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我在中山堂內外,徘徊良久,不禁頓生無限的滄桑之感。
臺北市區的範圍甚廣,比南京小,比蘇州大,但街道之建設,卻遠比南京、蘇州好。我們在臺北城中兜了大半個圈子,的確有些累;後來,我們在新臺公司附近一家糖菓店裡買點餅乾麵點等,便由泉州街龍口町一帶繞回植物園。於路過臺灣省參議會門口時,我們看到該會的窗口,忽然露出一大幅擁護蔣主席的白布。在前些日子,我們做夢也看不到那一大塊白布啊!而在臺北神社附近,我們又看到五六具屍體,東倒西歪的睡在路旁,雖然已經腐爛了,也無人聞問。由後門踏進植物園時,我們更看到在有些樹木的枝枒間,竟然掛著十幾塊炸碎的人肉。
這真是一種人類的慘痛,而也是一種民族的悲劇啊!
(四)新聞界空前的浩劫
自從國軍開到臺灣以後,新聞界便遭遇到空前的災難,和空前的浩劫。這責任不在國軍,因為,劉雨卿所部的二十一師,根本未曾逮捕任何記者。但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卻以在事變期間,臺灣大多數的報紙,均受異黨分子控制,散布謠言,煽動事變,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深中日本奴化思想之遺毒等等為理由,於3月9日,首先將中山路的《民報》予以查封,搗毀該報之印刷廠,並逮捕一部分工作之人員。至11日,臺北所有之民間報紙如《人民導報》、《中外日報》、《大明報》、《重建日報》、《國是日報》等亦先後被封閉。各報之負責人與重要之工作人員,均以「叛國」或「異黨」、「暴徒」等罪名而紛紛加以逮捕。如《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自從教育處副處長被免職以後即被拘押;此外如《民報》社長吳春霖,《重建日報》社長蘇泰皆,《中外日報》董事長林宗賢,《大明報》社長艾璐生、總編輯馬銳籌、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等新聞從業員,均一一被捕。即臺灣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所主辦之《國是日報》也不能倖免,林亦被禁閉一天始放出。至《重建日報》社長蘇泰皆,因中央有電到,後方釋放。即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主辦之《新生報》社,社長李萬居亦被打得頭破血流,至該報總編輯暨主要負責人均以在於事變時該報不聽指揮,擅自刊載二二八事件處委會之新聞,而遭逮捕;事後並大事整飭內部,重換新人。此外,如《上海大公報》駐臺辦事處也曾被封閉幾天始開禁。至京滬一帶駐臺記者,均紛紛化裝易服,改名換姓,躲在朋友家裡不敢出來。稍一不慎,即行失蹤。故一時臺北新聞界皆風聲鶴唳,日夜不安,人人自危。
臺北一地如此,其他各處亦莫不皆然。如基隆《自強報》、高雄《國聲報》、花蓮《東臺日報》,均被封閉,各主要負責人之命運亦同臺北一樣,不是逮捕,便是拘押。
是以,那時在臺北出版之報紙,只有《新生報》與《和平日報》兩家。迨至3月20日左右,連國防部所主辦之臺灣版《和平日報》,因為刊載南京二中全會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消息,亦被警備總司令部予以封閉,甚至於《和平日報》之文化服務部(書店性質)也遭查封,該報社長李上根及重要職員均被逮捕。警備部對外則說是奉國防部白部長崇禧的命令;但白部長於4月2日由臺返京在招待記者時,卻堅決否認此事,足見白部長未曾下令封閉報館。後來,《上海大公報》和《中央日報》的航空版,以及其他各地之報紙,如寄到臺灣時,均須受警備總司令部之檢查。凡不利於陳儀之新聞或言論,均一律被鏟版,故各報均常常開天窗,甚至於有些無關緊要之消息,亦被檢查員用油墨塗去或鏟掉。
直至我離開臺北時,臺北只剩下了一家官辦的《新生報》。至於中宣部所主辦之《中華日報》,僅能在臺南出版,臺北則不准發行。凡是被捕的新聞從業員,均下落不明,迄不知究拘何處?新聞界像這樣大規模的被逮捕,不僅世界罕聞,即在中國任何各地亦聞所未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