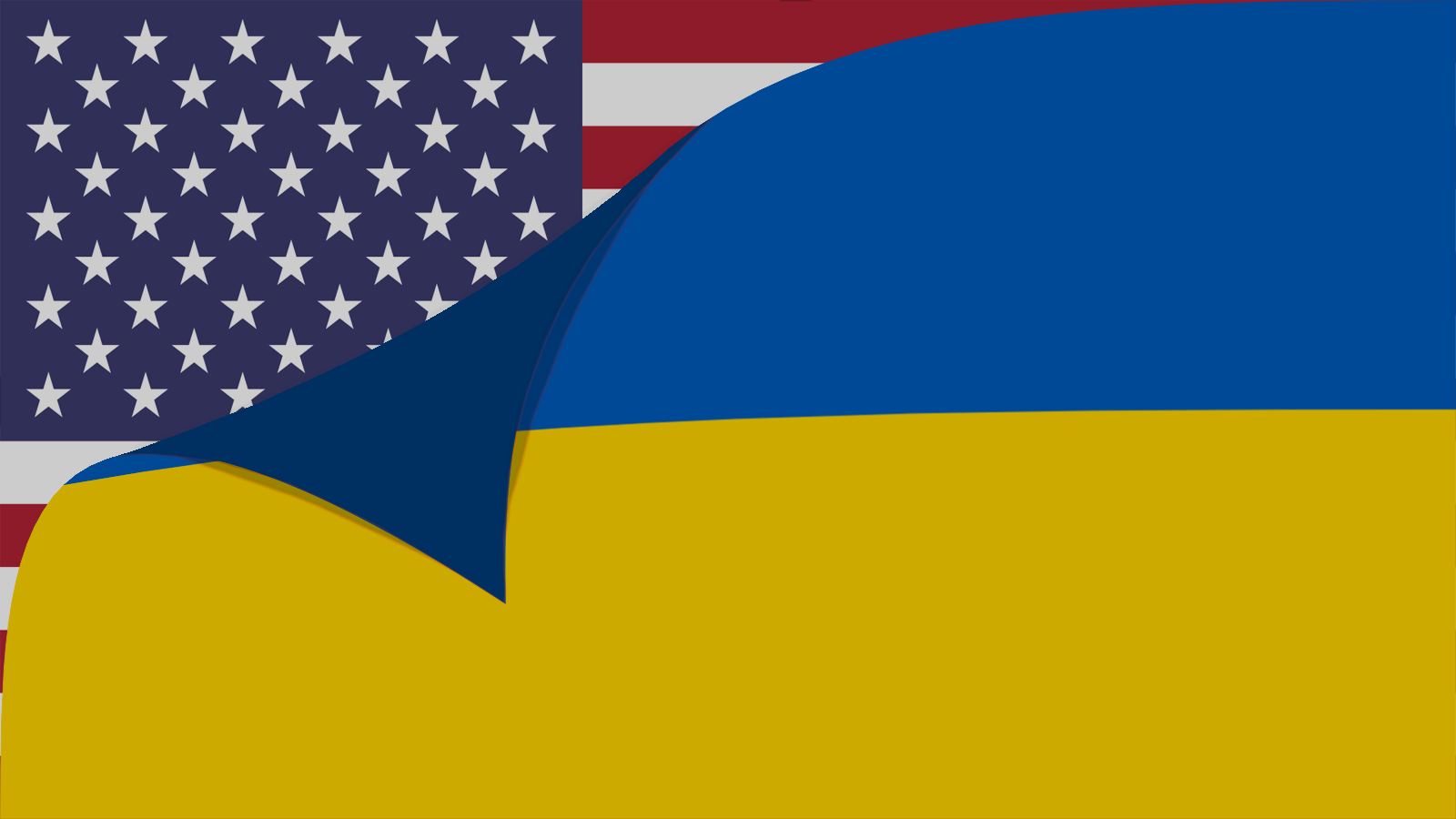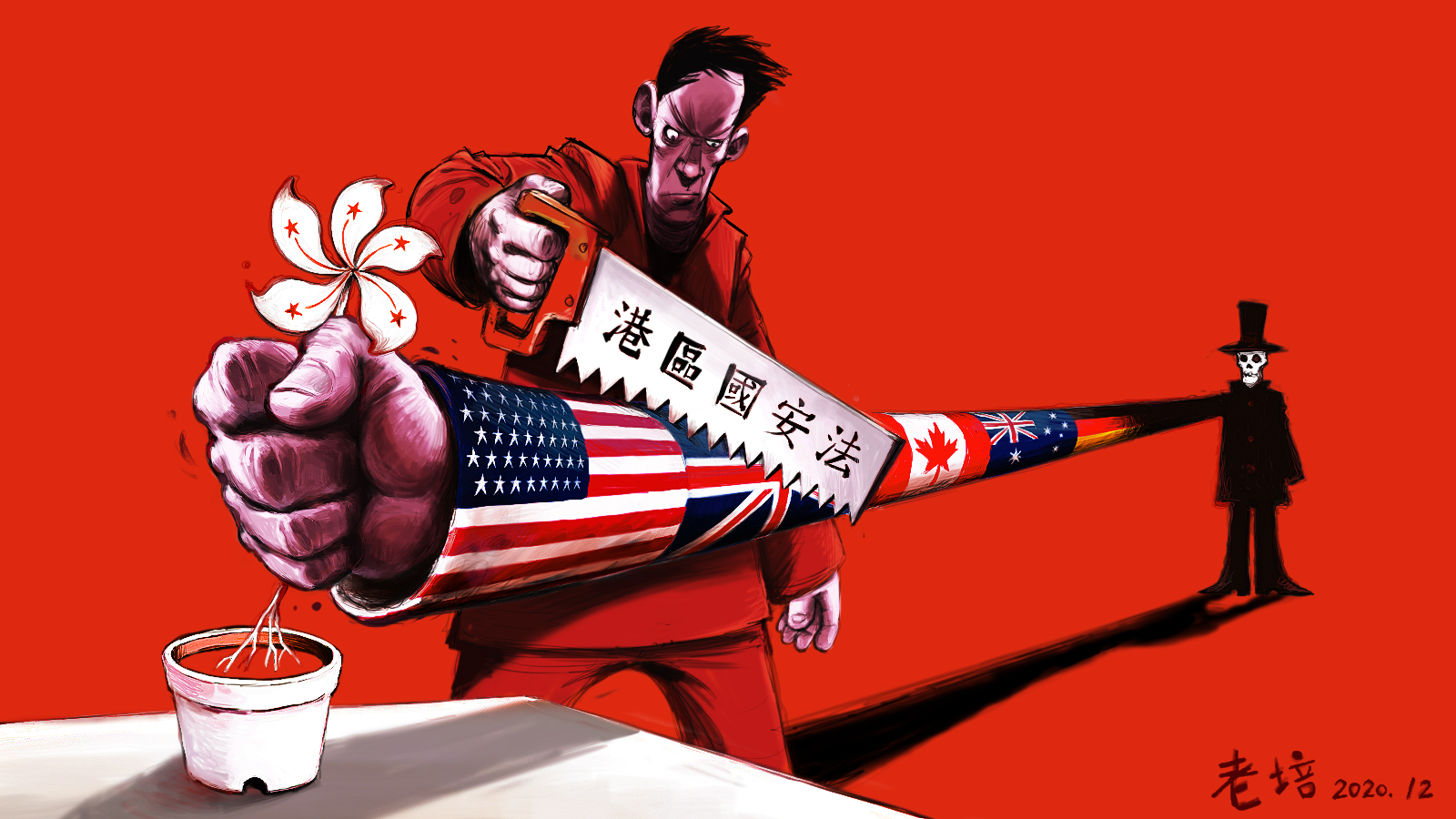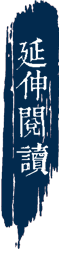講好中國故事是伴隨著中國的發展而凸顯的一個歷史性要求。客觀而言,還是中國的一個明顯的短板。那麼,講好中國故事的難點在哪裡呢?結合我自己的體會,認為有三點。
一、要發自內心的願意講,願意去辯護。
這是前提。現在很多知識菁英還做不到。這本質上是認同問題。目前看,相當數量的知識精英不認同中國的模式,而是認同西方。他們認同西方,就會自發的為西方辯護。比如川普當選,這是極其嚴重的美國和西方的黑天鵝事件。但清華的學者秦暉先生在環球時報年會上公開講,這說明美國是真民主。再比如,疫情在英國爆發時,英國提出群體免疫,結果在本國反對聲一片,但中國卻有媒體率先為之辯護,稱之為國情、科學道理。
我再舉一個中國學者的例子。就是北大憲政學者張千帆。他於2020年3月在《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於搖籃。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即便危機失控暴發,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能力也遠勝專制國家。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護下,能讓居民獲得疫情發展的準確信息;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各級民意代表能合理權衡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係,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確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並監督各級行政依法執行。遇到武漢肺炎這樣的嚴重疫情,憲政國家的民意代表絕對是閃現在各種場合的活躍人物,其忙碌程度不會亞於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
這次疫情,西方表現可謂災難性的,但認同他們的學者仍然自發地為之辯護。我曾把這段話寫到《巴黎日記》中,有讀者這樣評論:按張千帆先生的標準,只有中國才是民主憲政國家。福山說這是川普個人因素,不是制度問題。西方多家智庫和媒體每隔一段時間就搞出一個抗疫全球評比。第一次,是把德國排在第一,中國中游。第二次是澳大利亞搞出來的,德國和美國得分都很低,但這個排名沒有中國。其理由是中國數據不透明。第三次是《彭博社》搞出來的,美國第一。
我再舉一個法國的例子。法國衛生部長比贊在疫情爆發前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後來疫情爆發,她受到了很大的指責。為此她接受《世界報》採訪,透露早在1月就向總統和總理發出過警報。但沒有被採納。當時,我正在寫巴黎日記,預言第二天在法國社會極度不滿的情況下,這將是一個爆炸性新聞。不料第二天,在所有媒體包括網路上,這個議題完全消失。我能理解這種做法,因為在當時那個環境下,真有可能動搖國本。
可是當中國武漢爆發疫情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群體和媒體和西方對比一下的話,表現實在是差得太遠。正是由於很多知識精英包括媒體人不認同體制,體制對他們也不信任,不信任就會加以很多限制,這種限制又會反過來強化知識群體的不認同。成了惡性循環。
為什麼中國的知識群體很多人不認同中國模式?有幾個原因:一是中國崛起的時間還太短,硬實力沒有及時轉化成軟實力;二是美國和西方的軟實力很悠久了,絕非一件兩件事所能改變;三是我們自己還處於迅速發展階段,又是超大規模國家,問題也很多;四是對中國自己不瞭解,對一些現實不接受。我重點講第四點。
我們對中國國情不理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黨執政;二是對社會的控制;三是人治;四是政府權力太大,什麼都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且已寫入憲法,但是有不少知識分子並不認同。反對的理由不外是長期一黨執政會導致僵化、自滿,沒有有效的監督、糾錯和問責機制。當然中共執政七十年的事實和國際社會特別是和西方的對比已經證明,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比如疫情下的問責,中國有,西方沒有。中國七十年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失誤是計劃經濟。但我們的糾錯即轉向市場經濟的速度並不慢。印度同時和中國建國,同時搞計劃經濟。但中國是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印度直到九十年代中,才在中國的示範下轉向市場經濟。再比如說文革十年就結束了,美國打阿富汗戰爭竟然打了二十年,十年前就已經意識到是錯了,但付諸行動卻又用了十年。
除了事實層面,關鍵還是文化層面,特別是政治文化。中國五千年就是一個政治中心。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文明誕生之初是一個世俗社會,沒有宗教的地位,也沒有宗教龐大的勢力和政治權力抗衡;二是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打破貴族對權力的壟斷。魏國的李悝改革,就是廢除世襲貴族特權,選賢任能。秦國的商鞅改革也是如此。百里奚是楚國的一個奴隸,被秦國用五張羊皮換回,擔任丞相。後來中國又建立了科舉制。貴族在中國也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來挑戰政治力量。於是形成政治上僅有一個中心(皇權)獨大。
反觀西方,一直存在皇權、教權、貴族三方的博弈。甚至國王的婚姻也要由教皇批准。
從歷史上看,中國如果只有一個政治中心,社會就穩定,民眾安居樂業。如果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就會政治動盪,天下大亂,民眾流離失所。這個意識甚至體現在造字上。一個中心是「忠」,兩個中心是「患」。
政治學有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中國的文化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不管怎麼變化,要想發展和穩定,就只能是一個政治中心。中華民國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一直無法產生一個穩定的、強大的政治中心。
其次,對社會的控制我也是這樣理解的。中國的超大規模、多民族,使得穩定和統一成為政治和社會最為重要的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對社會的控制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在中國幾千年,控制永遠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考慮靈活性和活力。比如互聯網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任何違反這一規則的思路在中國肯定行不通。雖然控制的成本很高,但不控制或者控制失敗的成本更高。
三是人治。我在去法國留學和生活之前,認為中國早晚一天會成為法治社會。但到了法國之後才領悟到中國就是個人情社會,永遠不可能變為西方那樣的法治社會。這是我們文明的根本特點。就如同法國的浪漫、德國的嚴謹、英國的保守。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改了,就不再是自己。
這裡我可以講一下2014年在臺灣觀選的經歷。我當時帶了很多法國葡萄酒,但考慮到不夠,還需要在機場免稅店再買。銷售人員告知根據規定只能買一瓶,但我可以買兩瓶,並安慰說,海關只是抽檢。言外之意,概率很低,不會有事。當看到發票上醒目的黑體提示「旅客入境限攜帶免稅煙一條、酒一公升」後,我不由笑了。不過在北京,我就只能買一瓶,儘管北京海關並不查酒。然而出關時,極小概率的事情發生了:我來臺灣這麼多次,第一次被攔住抽檢!對方告知按規定超過限量的要沒收(超了7瓶),每瓶酒還要罰款2000新臺幣(約400人民幣)。然而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對方繼續說:你是第一次(不知從何知道),所以酒可以寄存在機場,離開臺灣時再帶走!也無需罰款!
來到機場大廳,到中華電信辦理當地手機。對方先問法國手機是否解過鎖。我聞言一愣:在法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偷偷地提供這項收費服務,法國是禁止的,所以也沒解過。對方一聽立即開始解鎖。見到中華電信這樣大牌、正規的公司如此做,還是大出我意外。也對臺灣的法治程度有了更深的理解。
隨後到機場郵局把在香港買的書寄到法國。當郵局人員知道這些書價值1800元人民幣,不由說到:「這麼貴啊。還是少寫吧,否則法國會認為你是在經銷,會讓你交稅的」。於是對方給我寫成5000台幣(1000人民幣)。這麼貼心的造假服務既讓我感動,更令人感慨中華文明強大的影響力。尋找制度的漏洞是我們不可磨滅、不可改變的基因。臺灣民主化二十多年,根本上對中國的國民性絲毫沒有改變。
這樣的「奇遇」還沒有結束,到旅館後,再一次讓我領略到文化特色。由於沒收到郵件確認,其中一天我重複訂了兩次,與旅館確認都收到後,我就想取消一次。但由於取消必須是在一週之前,我只能承擔全款。不料旅館說他們可以幫我做到,只要他們操作從我的信用卡扣款失敗就可以了。
很巧的是,當天的《中國時報》也在討論一個醫療問題,標題就是:「釐清情理法」。「情理法」這樣的排序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短短幾個小時連續發生的「奇遇」:既有政府(海關),也有企業(免稅店、電信公司、旅館),也有公共服務部門(郵局),在解決問題上所表現出的一致性是我們理解臺灣社會最好的鑰匙──那就是中國文化的人情特性。
四是政府權力太大,什麼都管。這也是西方經常批評或者攻擊中國的地方。但是在中國,權力很大什麼都管的並不僅僅是政府,家庭、單位也都是如此。在家庭,父母是無限責任,孩子未成年要管;成年了,上學,工作,結婚都要管,給他們買車買房。他們有了下一代,還要當貼錢的保姆。但在西方,孩子成人之後父母就不管了。我講一個法國的例子。孩子想假期出去旅遊,想讓爺爺奶奶幫著看一下孩子,他們不能直接說,否則肯定會被拒絕。於是他們說回家吃飯,飯後要走了才說去旅遊,要把孩子留下。這個時候父母即使不願意當然也不合適再把孩子趕走。當然父母老了,孩子也不管。法國獲得嘎呐電影大獎的電影《愛》有一個情節,母親在醫院,孩子去醫院看望,問父親:我能幫點什麼嗎?父親回答說:「沒有,沒有,你能來就很感謝了」。中國家庭如此,單位也是一樣。比如大學,不僅要管教學,還要管住宿、吃飯,還有醫療機構、超市。甚至學生在校外出事,也是學校的責任。但在法國,大學只管教學,其他一律不管。過去法國單位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下班後不宜再給員工打電話,後來直接立法。
中國從家庭、社會到政府,都是無限責任,西方則是有限責任。所以中國政府的權力很大,什麼都管。西方則相反。2021年美國發生嚴酷天氣,大量停電。民眾向政府求救。結果就有官員公開講,政府不欠他們的,他們應該自己解決。這不是官員混帳,而是他們的文化就是這樣。
最後我強調一點的是,我在法國生活二十多年,想明白一件事:中國的制度不管有多少不足,但這是唯一適合我們的模式,別無選擇。其他文明的模式,比如伊斯蘭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制度模式都不適合中國。伊斯蘭文明不適合中國,大家沒有意見,但西方模式不適合中國卻有很多人不認同。其實理由很多,只說一條:多民族國家實行西方的制度模式必然會解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如此。就是老牌的西方國家,如英國、加拿大、西班牙也都面臨同樣的國家分裂問題。美國甚至因為南方獨立而發生內戰。西方這種制度更適合在單一民族國家。像中國這樣多民族國家,必然解體。
二、當下的國際環境增大了講好中國故事的難度。
我2000年剛到法國時,法國媒體很少談中國,即使談到了,也往往比較客觀、正面。因為那個時期中國太弱,法國優越感很強,覺得中國這麼弱小,就沒有必要這麼苛刻了。但隨著中國的發展,法國媒體越來越聚焦中國,攻擊和抹黑成為主流。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對中國就是一邊倒的污名化了。特別是當法國疫情爆發時,媒體竟然也是第一時間不去反思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中國出現疫情後的一個多月時間,法國沒有吸取教訓做好準備,相反更是步調一致加大了對中國的攻擊?
當時中央學校一個朋友和我聯繫問中國在抗擊疫情上表現的這麼出色,法國媒體是不是有些反思,對中國有所肯定?他這個問題是正常的思路和邏輯,但現實卻完全相反。不僅法國,整個西方都是如此。
為什麼中國表現這麼好,卻仍然遭到西方全盤否定,原因在哪裡呢?
類似的問題我也曾問過法國和美國的漢學家。他們過去對中國還比較友好,但後來就突然都變了。他們回答的十分坦率,我們不能接受一個中國主導的世界。簡單講,這就是國家利益、地緣政治的博弈。
中國崛起的同時,西方恰在衰落,這增強了西方的危機感。我是研究政治制度的,非常清楚,政治制度就怕有替代性。西方一直試圖證明自己是唯一正確的模式,那麼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不用擔心動搖體制,也容易化解危機。所以講好中國故事已經不是改善中國形象、減少誤會那麼簡單,而是國家利益的博弈了。而國家利益博弈是不講道理的。今天的國際現實就是地緣政治取代學術,取代說理。我們即使願意講,也善於講,但也不會被西方所接受,它們可以封殺你的聲音,可以主導對中國的攻擊。
除了地緣政治,還有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是全球資源的有限性。歐巴馬在擔任總統時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時就公開講:假如中國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將對全球是災難。從道理上講,西方要求發展中國家向它學習,採用它的政治制度,理由之一就是可以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可以達到和超過西方。但對於西方自己以及取得成功的亞洲四小龍來說,其人口規模極小,地球的資源還是能夠承受。但中國有十四億人,這樣的規模實現現代化,在技術進步沒有重大突破的情況下,只能導致西方減少消費。這又會影響到西方制度的穩定和合法性。西方當然無法接受。
二是美國的特殊性。美國這個移民國家不但非常年青,而且還沒有主體民族,沒有文化傳統和民族層面的一致認同。在美國南部,甚至非英語是主流。國家要維持統一的難度很高,發生分裂和統一的內戰是極為正常的。目前美國維持統一主要是靠價值觀和所謂的發財致富的美國夢。但現在這兩個條件都在加速喪失。一旦美國被中國全面超越,它失去的不僅僅是全球霸主地位,甚至國家都極有可能不復存在。這是今天的美國和昔日的英國不同的地方。英國失去霸主地位,最嚴重的後果是喪失殖民帝國,但其本土仍然可以維持──當然如果進一步衰敗,蘇格蘭獨立總有一天會成真。
所以,中國提出要講好中國故事,西方則一定要講壞中國的好故事。
我舉幾個例子。中國提出命運共同體。西方就認為這是中國干預他國事務的一個藉口──我們是命運共同體了嘛,有事當然要管。再就是中國提出共建、共商、共享。西方的理解是:難道西方做什麼事還要先和中國商量嗎?我們的利益要和中國分享嗎?
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經濟領域也一樣。過去我們都認為西方是市場經濟、法治社會。企業只要質量好,服務好,價格低就能在西方站得住腳。結果華為、抖音的事件警醒了大家。我在法國曾和宇通公司的負責人交流過。她說過去電動大巴進入法國並不難,對手並不多。但後來競標時,哪怕他們的條件明明優於對手,也仍然被淘汰。後來才明白這是地緣政治問題。
今天國際環境的複雜性不僅僅在於中國和西方的對立,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也不友好,也加入了西方發起的輿論戰。當然它們的原因和動機與西方不同,在那發展中國家間對中國的抹黑攻擊也各有不同。一是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它們擔心時間在中國一邊,如果現在不出手,等到中國崛起完成,將來會一無所獲得。這包括越南、印度、菲律賓等。二是有些國家長期受西方支配,利益和西方緊密,它們或者為了獲得西方更大的支持,或者乾脆就是西方授意,而一定程度加入了對中國的抹黑行列。比如泰國、印尼、巴西、立陶宛。三是有的發展中國家和中國少數民族有一定的關係,對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不認同。這方面的國家主要有土耳其。四是有的國家在一些政策方面反對中國並不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第三方因素。比如波蘭,對俄羅斯非常恐懼和仇視,只要是對俄羅斯不利的事情都支持,而中國和俄羅斯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約定這是一種僅限中俄之間的關係,其他國家都不再使用這種概念關係),所以波蘭有時也會加入對中國的抹黑。
發展中國家加入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對國際社會有一定的欺騙性,會認為中國確實做的不對,是以大欺小。
三、我們內宣水平很高,但外宣水平差距很大。
這除了不少知識精英不認同體制不願意為中國辯護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瞭解西方。中國的學者群體有兩個先天不足。一是多數沒有在體制內工作的經驗。也就是說對中國本身的瞭解不夠,尤其是政治層面,其瞭解更多的是在於書本。二是雖然很多學者有國外留學、進修的經歷,但是僅限於從校園到校園。他們對西方的瞭解很有限。我上文提到的張千帆教授離譜的文章就是一例。
我們中國研究院為什麼這麼多年能異軍突起,就在於我們主要人員既有體制內的工作經驗,又有西方長期生活的積累。不僅真正的瞭解中國,也瞭解西方。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張維為院長能夠就講好中國故事這個話題在政治局講課。但中國研究院只是一個特例,並不具備普遍性。
當然,我們的體制也有許多要改正的地方。我就舉兩個例子。一是我在法國經常接待國內的代表團,招商、引智。但他們播放的短片或者散發的材料都有問題。我曾問過他們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是給國外看的,還是給國內看的,特別是領導看的?他們想想之後也承認確實是給國內看的。這樣的思路做出來的東西,怎麼在國外會有效果?比如對學者講話要寬容,講好中國故事是一個需要學習和提高的過程,講錯了也不要緊。應該給予學者更大的空間。
正是由於這三大問題,講好中國故事和捍衛中國的話語權過程中出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中國的外交官衝在了第一線。當然也立即被西方扣上「戰狼」外交的帽子。中國的外交人員衝上第一線有它的優勢:一是信念堅定,他們的職業就是捍衛中國利益。二是瞭解西方情況,抓得准,回應迅速。三是外交人員影響力大,西方很難利用自己在話語權上的優勢進行完全封殺,往往能傳播出去。但這樣也有缺點:他們代表國家,必須和國家的立場嚴格一致,沒有回旋餘地。出了錯,很容易上升到國家層面,成為外交事件。更何況外交職能就是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在衝突第一線和對方對打。
我舉一個例子。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香港修例事件中接受BBC訪談,被問到修例是否可能取消。劉曉明立即回答道:不可能取消,這麼好的法案,得到香港多數人的支持,為什麼要取消。結果幾天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就宣佈取消修例。這嚴重傷害了中國外交的公信力。
西方衝在第一線的都是媒體和學者,他們錯了就錯了,也沒什麼。所以他們也敢瞎說。尺度也不控制。中國外交人員則不行。
上述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時間,從可預見的未來,被抹黑和攻擊是中國崛起的一個副產品,很難徹底消失。今天的美國其實也是被罵得最多的國家。中國最終需要解決的是不怕挨駡的問題。中國只要持續良好發展,處理好自己的內部事務,講好中國故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其他的問題都能夠水到渠成的找到辦法。